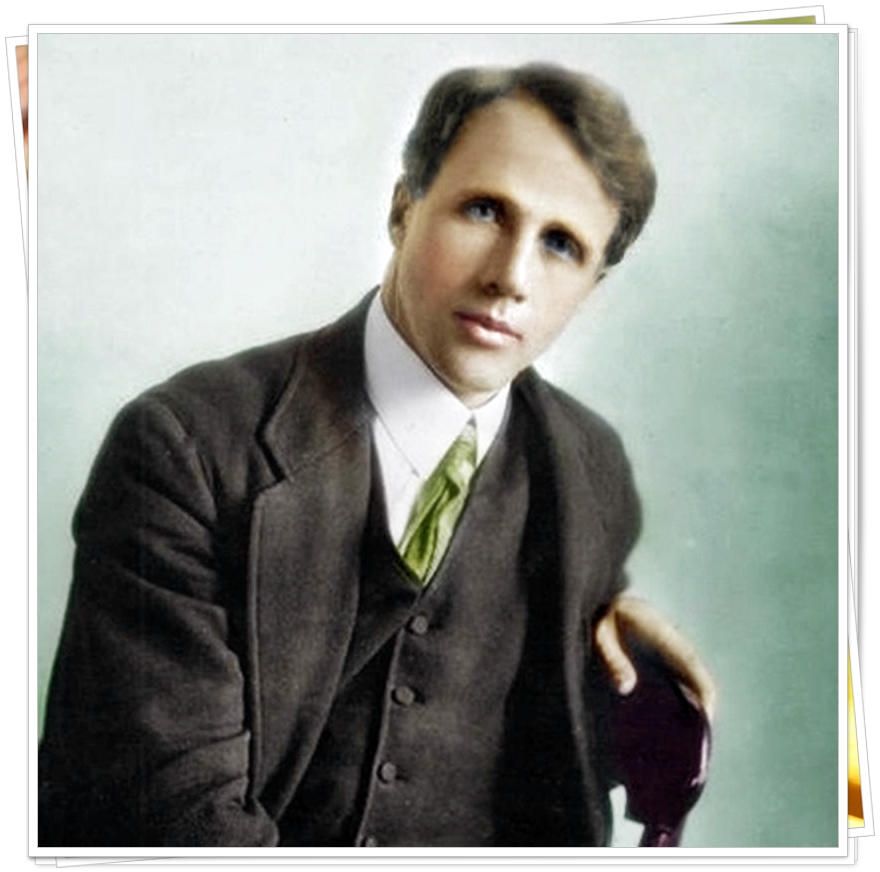早年生活與家庭
金斯伯格出生於新澤西州紐瓦克市的一個猶太[17]家庭,並在附近的帕特森長大。[18] 他是父親路易斯·金斯伯格的次子,父親也出生於紐瓦克,是一位教師和出版詩人;母親原名娜奧米·利維,出生於俄羅斯涅韋爾,是一位狂熱的馬克思主義者。[19]
青少年時期,金斯伯格開始給《紐約時報》寫信,探討政治問題,例如二戰和工人權利。[20] 他在《帕特森晨報》上發表了他的第一首詩。[21] 高中時期,受老師熱情洋溢的朗讀啟發,金斯伯格對沃爾特·惠特曼的作品產生了興趣。[22] 1943年,金斯伯格從東區高中畢業,在蒙特克萊爾州立學院短暫就讀,之後憑藉帕特森青年希伯來協會的獎學金進入哥倫比亞大學。金斯伯格原本打算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法律,但後來改主修文學。[19]
1945年,他加入商船隊,以賺取在哥倫比亞大學繼續深造的學費。[23] 在哥倫比亞大學期間,金斯伯格為文學期刊《哥倫比亞評論》和幽默雜誌《小丑》撰稿,榮獲伍德伯里詩歌獎,擔任愛樂協會(文學和辯論團體)主席,並加入了野豬頭協會(詩歌協會)。[22][24] 他住在哈特利樓,傑克·凱魯亞克和赫伯特·戈爾德等「垮掉的一代」詩人也曾居住於此。[25][26] 金斯伯格曾表示,他最喜歡的哥倫比亞大學課程是大學一年級必修的「偉大著作」(由萊昂內爾·特里林講授)。1948年,他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獲得英語和美國文學學士學位。[27]
據詩歌基金會稱,金斯伯格在一次聽證會上聲稱自己精神錯亂,隨後在精神病院待了幾個月。據稱,他因在宿舍藏匿贓物而被起訴。據稱,被盜財物並非金斯伯格所有,而是屬於一位熟人的。[28] 金斯伯格還參加了鮑厄里聖公會聖馬可教堂的公開朗誦會,該教堂後來在他去世後為他舉行了追悼會。[29][30]
與父母的關係
金斯伯格在1985年的一次採訪中稱他的父母是「老式的熟食店哲學家」。[18] 他的母親也是一名活躍的共產黨員,經常帶金斯伯格和他的弟弟尤金參加黨的會議。金斯伯格後來回憶說,他的母親「編造的睡前故事都大體是這樣的:『善良的國王騎馬從城堡里出來,看到受苦的工人,並治癒了他們。』」[20] 談到他的父親,金斯伯格說道:「我的父親會在家裡走來走去,要麼低聲吟誦艾米莉·狄金森和朗費羅的作品,要麼攻擊T·S·艾略特用他的『蒙昧主義』毀掉了詩歌。我對這兩種說法都產生了懷疑。」[18]
金斯伯格的母親娜奧米·金斯伯格患有精神分裂症,其癥狀常常表現為偏執妄想、思維紊亂和多次自殺未遂。[31] 例如,她會聲稱總統在家裡植入了竊聽器,而她的婆婆正試圖殺死她。[32][33]娜奧米對周圍人的懷疑,導致她與年幼的艾倫(比爾·摩根在其金斯伯格傳記《我慶祝自己:艾倫·金斯伯格的某種私人生活》中稱之為「她的小寵物」)的關係更加密切。[34] 她還試圖割腕自殺,不久后被送往格雷斯通精神病院;金斯伯格的大部分青春歲月都在精神病院度過。[35][36] 他與母親以及母親精神疾病的經歷,是他創作兩部主要作品《嚎叫》和長篇自傳體詩《獻給娜奧米·金斯伯格的卡迪什(1894-1956)》的主要靈感來源。[37]
初中時,他陪母親乘公共汽車去看心理醫生。這次旅行深深地困擾著金斯伯格——他在《卡迪什》中提到了這次旅行以及童年時期的其他時刻。[38] 他與母親的精神疾病以及她被送進精神病院的經歷,在《嚎叫》中也多次被提及。例如,「朝聖者州立、羅克蘭和灰石的惡臭大廳」指的是他母親和卡爾·所羅門經常光顧的機構,而這首詩表面上是這首詩的主題:紐約州的朝聖者州立醫院和羅克蘭州立醫院,以及新澤西州的灰石公園精神病院。[34][39][40] 緊接著是「母親終於******」這句話。金斯伯格後來承認,刪除的是髒話「操」。[39] 他在第三部分還提到所羅門:「我和你一起在羅克蘭,你模仿我母親的影子」,再次表明了所羅門和他母親之間的聯繫。[41]
金斯伯格在母親去世后收到了一封回信,回信是他寄給她的《嚎叫》的副本。信中告誡金斯伯格要乖乖聽話,遠離毒品;她說:「鑰匙在窗戶上,鑰匙在窗戶的陽光里——我有鑰匙——艾倫,結婚吧,別吸毒——鑰匙在酒吧里,在窗戶的陽光里。」
在她寫給金斯伯格弟弟尤金的信中,她寫道:「上帝的線人來到我的床邊,我在天空中看到了上帝本人。陽光也照耀著我,一把鑰匙掛在窗戶邊,讓我可以出去。陽光的黃色也照亮了窗戶邊的鑰匙。」[43] 這些信件以及缺乏誦讀卡迪什(Kaddish)的設施,激發了金斯伯格創作《卡迪什》(Kaddish)。其中引用了娜奧米生活中的許多細節、金斯伯格與她相處的經歷以及這封信,包括「鑰匙在光明中」和「鑰匙在窗戶里」這兩句話。[44]
紐約節拍
本節需要更多引文以作核實。請在此部分添加可靠來源的引文,以幫助我們改進本文。未註明來源的材料可能會受到質疑和刪除。 (2024年8月)(了解如何以及何時刪除此消息)
金斯伯格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第一年結識了本科同學盧西安·卡爾,後者將他介紹給了多位未來的「垮掉的一代」作家,包括傑克·凱魯亞克、威廉·S·巴勒斯和約翰·克萊倫·霍姆斯。他們之所以結緣,是因為他們彼此都看到了對美國青年潛力的熱情,這種潛力超越了二戰後麥卡錫時代美國嚴格的墨守成規。[45] 金斯伯格和卡爾激動地談論著對文學和美國的「新視野」(這一短語改編自葉芝的《一個視野》)。卡爾還將金斯伯格介紹給了尼爾·卡薩迪,金斯伯格對他一直心存迷戀。[46] 凱魯亞克在其1957年的小說《在路上》的第一章中描述了金斯伯格和卡薩迪的相遇。[38]凱魯亞克將他們視為「新視野」中陰暗的一面(金斯伯格),光明的一面(卡薩迪)。這種看法部分源於金斯伯格與共產主義的聯繫,而凱魯亞克對共產主義的懷疑日益加深。儘管金斯伯格從未加入過共產黨,但凱魯亞克在《在路上》中稱他為「卡洛·馬克思」。這成為他們關係緊張的一個原因。[22]
此外,在紐約,金斯伯格在小馬廄酒吧遇到了格雷戈里·科索。科索當時剛從監獄獲釋,得到了小馬廄酒吧顧客的支持,並在他們見面的當晚在那裡寫詩。金斯伯格聲稱,他立刻就被科索吸引,科索是異性戀,但在監獄服刑三年後,他理解了同性戀。金斯伯格在閱讀科索的詩歌時更加震驚,意識到科索「精神上天賦異稟」。金斯伯格把科索介紹給了他其他的核心圈子。在馬廄的第一次見面中,科索給金斯伯格看了一首詩,詩中描繪的是一位住在他街對面、在窗邊裸體曬太陽的女子。令人驚訝的是,這位女子恰好是金斯伯格的女友,金斯伯格在一次異性戀嘗試中與她同居。金斯伯格把科索帶到了他們的公寓。在那裡,這位女子向年紀尚輕的科索求愛,科索害怕地逃走了。金斯伯格把科索介紹給了凱魯亞克和巴勒斯,他們開始一起旅行。金斯伯格和科索成為了終生的朋友和合作夥伴。[47][需要更多引文]
在金斯伯格人生的這段時期結束后不久,他通過巴納德學院的哲學教授亞歷克斯·格里爾認識了艾麗絲·納達·考恩,並與之發展了一段戀情。亞歷克斯·格里爾在「垮掉的一代」蓬勃發展的時期曾與金斯伯格交往過一段時間。在巴納德學院讀書期間,艾麗絲·考恩廣泛閱讀了埃茲拉·龐德和T·S·艾略特的詩歌,並結識了喬伊斯·約翰遜、利奧·斯基爾等「垮掉派」詩人。[引文需要]考恩大部分時間都對較為陰暗的詩歌情有獨鍾,而「垮掉派」詩歌似乎也為她提供了某種魅力,讓她得以窺見人格中陰暗的一面。在巴納德學院期間,考恩加入了一個由反建制藝術家和空想家組成的小團體,外人稱之為「垮掉的一代」,因此獲得了「垮掉的愛麗絲」的綽號。她在學院最早認識的一位朋友是「垮掉的一代」詩人喬伊斯·約翰遜,後者後來在她的著作中刻畫了考恩的形象,包括《次要人物》和《來跳舞吧》,這兩本書分別講述了兩位女性在巴納德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垮掉的一代」群體中的經歷。[引文需要]通過與艾麗絲·考恩的交往,金斯伯格發現他們有一位共同的朋友——卡爾·所羅門,後來他把自己最著名的詩歌《嚎叫》獻給了他。這首詩被認為是金斯伯格 1955 年之前的自傳,並通過他與當時其他垮掉的一代藝術家的關係,簡要介紹了垮掉的一代的歷史。
「布萊克幻覺」
1948年,金斯伯格在東哈萊姆區的一間公寓里,一邊自慰一邊閱讀威廉·布萊克的詩歌,突然出現了幻聽[48],他後來稱之為「布萊克幻覺」。金斯伯格聲稱聽到了上帝的聲音——也被描述為「亘古常在者的聲音」——或者布萊克本人朗讀《啊!向日葵》、《病玫瑰》和《迷失的小女孩》。這種體驗持續了數天,他相信自己見證了宇宙的互聯互通;金斯伯格回憶說,在看了公寓消防梯上的格子結構,然後又看了看天空后,他直覺地認為其中一個是人類製造的,而另一個是他自己製造的。[49] 他解釋說,這種幻覺並非由吸毒引起,而是他後來試圖用各種藥物來重拾那種互聯互通的感覺。[22]後來,在1955年,他在詩歌《向日葵經》中提到了他的「布萊克幻象」,寫道:「——我如痴如醉地衝上前去——這是我的第一朵向日葵,關於布萊克的回憶——我的幻象——」。[50]
舊金山文藝復興
金斯伯格於20世紀50年代移居舊金山。在1956年《嚎叫及其他詩歌》由城市之光出版社出版之前,他曾擔任市場研究員。[51]
1954年,金斯伯格在舊金山結識了彼得·奧洛夫斯基(1933-2010),並愛上了他,後者成為了他的終身伴侶。[22]他們的通信選段已經出版。[52]
同樣在舊金山,金斯伯格結識了舊金山文藝復興時期的成員(詹姆斯·布勞頓、羅伯特·鄧肯、瑪德琳·格里森和肯尼斯·雷克斯羅斯),以及其他後來被廣泛歸類為「垮掉的一代」的詩人。金斯伯格的導師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給舊金山文藝復興時期的領軍人物肯尼斯·雷克斯羅斯寫了一封介紹信,後者隨後將金斯伯格引入了舊金山詩壇。[53] 在那裡,金斯伯格還結識了三位在里德學院結識的嶄露頭角的詩人和禪宗愛好者:加里·斯奈德、菲利普·惠倫和盧·韋爾奇。1959年,金斯伯格與詩人約翰·凱利、鮑勃·考夫曼、A·D·維南斯和威廉·馬戈利斯共同創辦了詩歌雜誌《福祉》(Beatitude)。
1955年中期,畫家兼六畫廊聯合創始人沃利·赫德里克找到金斯伯格,請他在六畫廊組織一場詩歌朗誦會。起初,金斯伯格拒絕了,但當他寫完《嚎叫》的草稿后,用他的話說,他「他媽的改變了主意」。[45]金斯伯格將活動宣傳為「六位詩人在六畫廊」。「垮掉的一代」神話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簡稱為「六畫廊朗誦會」,於1955年10月7日舉行。[54]這場活動本質上彙集了東西海岸「垮掉的一代」的現實情況。對金斯伯格個人而言,當晚的朗誦會更有意義,其中包括《嚎叫》的首次公開朗誦,這首詩為金斯伯格以及與他相關的許多詩人帶來了世界性的聲譽。凱魯亞克的小說《達摩流浪者》中描述了那晚的情景,描述了人們如何從觀眾那裡收集零錢來買酒,以及金斯伯格如何張開雙臂,激情洋溢、醉醺醺地朗讀。
金斯伯格里程碑式詩集《嚎叫及其他詩歌》(1956)初版封面
金斯伯格的主要作品《嚎叫》以其開篇之語而聞名:「我看到我們這一代最優秀的思想被瘋狂摧毀,飢餓、歇斯底里、赤身裸體……」。《嚎叫》在出版時因其粗俗的語言而被認為是醜聞。1956年,它在舊金山城市之光書店出版后不久,就因涉嫌淫穢而被禁。這項禁令在《第一修正案》的捍衛者中引起了轟動,後來,在克萊頓·W·霍恩法官宣布這首詩具有可取的藝術價值后,禁令得以解除。[22]金斯伯格和因販賣《嚎叫》而入獄的城市之光樂隊經理 Shig Murao 成為了終生的朋友。[55]
《嚎叫》中的傳記引用
金斯伯格曾聲稱,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一部延伸的傳記(就像凱魯亞克的《杜洛茲傳奇》一樣)。《嚎叫》不僅是金斯伯格1955年之前經歷的傳記,也是一部「垮掉的一代」的歷史。金斯伯格後來還聲稱,《嚎叫》的核心是他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母親未解決的情感。儘管《卡迪什》更明確地描寫了他的母親,但《嚎叫》在很多方面也受到了同樣的情感驅動。《嚎叫》記錄了金斯伯格一生中許多重要友誼的發展。這首詩的開頭是「我目睹我們這一代最優秀的思想被瘋狂摧毀」,這為金斯伯格描寫卡薩迪和所羅門奠定了基礎,並將他們永垂不朽地載入美國文學。[45]這種瘋狂是社會運轉所需的「憤怒的解藥」——瘋狂是它的疾病。在詩中,金斯伯格聚焦於「卡爾·所羅門!我與你同在羅克蘭」,從而將所羅門塑造成一個尋求擺脫「束縛」的典型人物。儘管他大部分詩歌中的引用都揭示了他的生平、他與其他「垮掉的一代」成員的關係以及他自身的政治觀點,但他最著名的詩歌《嚎叫》或許仍然是最好的起點。[需要引用]
去巴黎和「垮掉的一代」旅館,丹吉爾和印度
1957年,金斯伯格離開舊金山,震驚了文壇。在摩洛哥待了一段時間后,他和彼得·奧洛夫斯基在巴黎加入了格雷戈里·科爾索的行列。科爾索把他們介紹到吉特勒-科烏爾街9號一家酒吧樓上的一間破舊的寄宿公寓,後來被稱為「垮掉的一代」旅館。很快,巴勒斯等人也加入了他們。對他們所有人來說,那都是一段富有成效、充滿創造力的時光。在那裡,金斯堡開始創作他的史詩《卡迪什》(Kaddish),科爾索創作了《炸彈與婚姻》(Bomb and Marriage),而巴勒斯(在金斯堡和科爾索的幫助下)則將之前的作品整合成《裸體午餐》(Naked Lunch)。這段時期被攝影師哈羅德·查普曼記錄下來。他大約在同一時期搬進了這家「旅館」,並不斷拍攝旅館里的住戶,直到1963年旅館關閉。1962年至1963年間,金斯堡和奧爾洛夫斯基遊歷了印度各地,在加爾各答(現加爾各答)和貝拿勒斯(瓦拉納西)各住半年。在前往印度的途中,他在雅典停留了兩個月(1961年8月29日至1961年10月31日),期間他參觀了德爾斐、米奇內斯、克里特島等地,然後繼續他的旅程,前往以色列、肯亞,最終抵達印度。[56]在此期間,他還與當時一些傑出的孟加拉青年詩人建立了友誼,其中包括沙克蒂·查托帕迪亞伊(Shakti Chattopadhyay)和蘇尼爾·甘戈帕迪亞伊(Sunil Gangopadhyay)。金斯伯格在印度擁有多位政界人士,其中最著名的是普普爾·賈亞卡爾(Pupul Jayakar),在當局急於驅逐他時,他幫助金斯伯格延長了在印度的居留時間。
英國與國際詩歌的化身
1965年5月,金斯伯格抵達倫敦,並表示願意在任何地方免費朗誦他的詩歌。[57]抵達后不久,他在「更好的書店」(Better Books)舉辦了一場朗誦會。傑夫·納托爾(Jeff Nuttall)稱其為「給飽受摧殘的集體心靈帶來的第一陣治癒之風」。[57] 湯姆·麥格拉斯(Tom McGrath)寫道:「這很可能成為英國歷史上——或者至少是英國詩歌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
書店朗誦會結束后不久,國際詩歌化身活動[58]的計劃就已醞釀,該活動於1965年6月11日在倫敦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舉行。活動吸引了7000名觀眾,他們聆聽了包括金斯伯格、阿德里安·米切爾、亞歷山大·特羅基、哈里·費恩萊特、安瑟姆·霍洛、克里斯托弗·洛格、喬治·麥克白、格雷戈里·科索、勞倫斯·費林蓋蒂、邁克爾·霍洛維茨、西蒙·文肯諾格、斯派克·霍金斯和湯姆·麥格拉斯在內的眾多名人的朗誦、現場和錄音表演。此次活動由金斯伯格的好友、電影製片人芭芭拉·魯賓組織。[59][60]
彼得·懷特黑德用膠片記錄了此次活動,並將其命名為《完全共融》(Wholly Communion)。英國的洛里默出版社和美國的格羅夫出版社也出版了一本同名書籍,其中包含電影中的圖片和一些當時表演的詩歌。
持續的文學活動
金斯伯格與他的伴侶、詩人彼得·奧洛夫斯基。照片拍攝於1978年
雖然「垮掉的一代」一詞最準確地指金斯堡及其密友(科爾索、奧洛夫斯基、凱魯亞克、巴勒斯等),但「垮掉的一代」一詞也與金斯堡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結識並結交的許多其他詩人聯繫在一起。這一術語的一個關鍵特徵似乎是與金斯堡的友誼。與凱魯亞克或巴勒斯的友誼或許也適用於此,但這兩位作家後來都努力與「垮掉的一代」這個名稱劃清界限。他們對這一術語的不滿部分源於將金斯堡誤認為是其領袖。金斯堡從未聲稱自己是某個運動的領袖。他聲稱,這一時期與他結交的許多作家都擁有許多相同的意圖和主題。這些朋友包括:大衛·阿姆拉姆、鮑勃·考夫曼;黛安·迪·普里瑪;吉姆·科恩;與黑山學院相關的詩人,例如查爾斯·奧爾森、羅伯特·克里利和丹尼斯·萊弗托夫;與紐約學派相關的詩人,例如弗蘭克·奧哈拉和肯尼斯·科赫。勒羅伊·瓊斯,後來改名為阿米里·巴拉卡,他在讀完《嚎叫》后,用一張衛生紙給金斯伯格寫了一封信。巴拉卡的獨立出版社圖騰出版社出版了金斯伯格的早期作品。[61][需要補充引文]在巴拉卡組織的一次聚會上,金斯伯格結識了蘭斯頓·休斯,當時奧內特·科爾曼正在演奏薩克斯管。[62]
與鮑勃·迪倫(猶太人)的肖像,攝於1975年
金斯伯格晚年在20世紀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運動和20世紀60年代的嬉皮士運動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與蒂莫西·利里、肯·克西、亨特·S·湯普森和鮑勃·迪倫等人成為朋友。金斯伯格去世前幾個月,在舊金山海特-阿什伯里街區的一家書店「書匠」(Booksmith)舉行了最後一次公開朗讀。[63] 1993年,金斯伯格訪問了緬因大學奧羅諾分校,向90歲的卡爾·拉科西致敬。
佛教與奎師那( Krishna)
另見:A. C. 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和咒石舞
1950年,凱魯亞克開始學習佛教[65],並與金斯伯格分享了他從德懷特·戈達德的佛教聖經中學到的知識。[65] 金斯伯格正是在那時第一次聽說了四聖諦和《金剛經》等經典。金斯伯格的支持幫助奎師那運動在紐約的波西米亞文化中建立起來。
金斯伯格的精神之旅始於早期自發的幻覺,並延續到早年與加里·斯奈德的印度之旅。[65] 斯奈德曾在京都大德寺第一禪學院學習。斯奈德一度吟誦般若波羅蜜多經,用金斯伯格的話來說,「這讓我大開眼界」。金斯伯格對此產生了興趣,前往隆德寺拜見達賴喇嘛和噶瑪巴。金斯伯格繼續他的旅程,在噶倫堡遇見了敦珠仁波切,敦珠仁波切教導他:「如果你看到可怕的事物,不要執著它;如果你看到美好的事物,也不要執著它。」
回到美國后,他在紐約市的一條街頭偶然遇到了秋陽創巴仁波切(兩人試圖搭乘同一輛計程車),[67] 秋陽創巴仁波切是一位噶舉派和寧瑪派的藏傳佛教大師,這促使他成為了秋陽創巴仁波切的摯友和終身導師。[65] 金斯伯格幫助創巴仁波切和紐約詩人安妮·沃爾德曼在科羅拉多州博爾德市的那洛巴大學創辦了傑克·凱魯亞克無形詩學學院。
金斯伯格也參與了克里希納教。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他開始將念誦哈瑞·奎師那真言融入到他的宗教實踐中。在得知西方世界哈瑞奎師那運動的創始人A. C. 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在紐約租了一家店面后,他與帕布帕德結為好友,經常拜訪他,並推薦出版商出版他的書籍,一段富有成果的友誼由此開啟。薩茨瓦魯帕·達薩·哥斯瓦米在其傳記《聖帕布帕德·利拉姆塔》中記錄了這段關係。金斯伯格捐贈了金錢、物資和自己的名譽,幫助這位斯瓦米建立了第一座神廟,並陪同他四處巡迴宣傳他的事業。
艾倫·金斯伯格在舊金山國際機場迎接A. C. 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 1967年1月17日
儘管金斯伯格不同意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的許多禁令,但他經常公開吟唱哈瑞·奎師那真言,將其作為自己哲學的一部分[69],並宣稱這能帶來一種狂喜的狀態。[70] 他很高興看到來自印度的正宗斯瓦米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正試圖在美國傳播這種唱誦。金斯伯格與蒂莫西·利里、加里·斯奈德和艾倫·沃茨等反主流文化思想家一起,希望將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和他的唱誦融入嬉皮士運動,並同意參加「真言搖滾舞會」,將這位斯瓦米介紹給海特-阿什伯里的嬉皮士社區。
1967年1月17日,金斯伯格協助策劃並組織了在舊金山國際劇院為巴克提維丹塔·斯瓦米舉辦的招待會。
音樂和吟誦都是金斯伯格詩歌朗誦時現場表演的重要組成部分。[76] 他經常用簧風琴自奏,也常有吉他手伴奏。據信,印度佛教詩人納加爾俊(Nagarjun)在貝拿勒斯向金斯伯格介紹了簧風琴。據馬萊·羅伊·喬杜里(Malay Roy Choudhury)稱,金斯伯格在向親戚學習時,包括向他的表妹薩維特里·班納吉(Savitri Banerjee)學習,從而完善了自己的演奏技巧。[77] 1968年9月3日,金斯伯格在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主持的電視節目《火線》(Firing Line)中詢問他是否能唱一首讚美克里希納神的歌,巴克利同意了,詩人一邊用簧風琴悲傷地演奏,一邊緩緩吟誦。據巴克利的同事理查德·布魯克希瑟 (Richard Brookhiser) 稱,主持人評論說這是「我聽過的最輕鬆自然的克里希納 (Krishna) 的歌」。[78]
在1967年舊金山金門公園舉行的人類聚會 (Human Be-In)、1968年芝加哥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以及1970年耶魯大學校園舉行的黑豹黨集會上,艾倫都通過音響系統連續數小時反覆吟唱「唵」。[79]
金斯伯格在歌曲《貧民窟被告》(Ghetto Defendant) 中吟誦《心經》,進一步將咒語帶入搖滾樂的世界。這首歌收錄於英國第一波朋克樂隊 The Clash 1982年的專輯《戰鬥搖滾》(Combat Rock) 中。
Mantra-Rock Dance 宣傳海報以艾倫·金斯堡 (Allen Ginsberg) 和主要搖滾樂隊為特色。
金斯伯格與孟加拉的飢餓主義詩人取得了聯繫,尤其是馬來人羅伊·喬杜里 (Roy Choudhury),後者向金斯伯格介紹了印度皇帝賈拉勒丁·穆罕默德·阿克巴 (Jalaluddin Mohammad Akbar) 的「三頭魚」。三條魚象徵著所有思想、哲學和宗教的共存。[80]
儘管金斯伯格對東方宗教頗有好感,但記者簡·克萊默認為,他和惠特曼一樣,信奉一種「美國式的神秘主義」,這種神秘主義「植根於人文主義,以及浪漫而富有遠見的人類和諧理想」。[81]
艾倫·金斯伯格遺產管理委員會與寶石之心國際組織於2021年在紐約市美國西藏之家合作舉辦了「轉變思想:至尊格勒仁波切與友人」展覽,這是一個畫廊和在線展覽,展出了艾倫·金斯伯格的學生格勒仁波切的照片。金斯伯格與格勒仁波切有著「不解之緣」。[82][83] 金斯伯格在斯坦福大學的照片檔案中展出了50張底片,以頌揚「艾倫和仁波切之間的獨特關係」。展覽精選了包括達賴喇嘛、藏學家和學生在內的眾多西藏大師,這些從未公開過的照片「都參考了艾倫在接觸印版和他圈出準備印刷的照片上所做的大量筆記」。[84]
疾病與逝世
1960年,他因熱帶疾病接受治療,據推測,他因醫生注射的未消毒針頭感染了肝炎,這導致了他37年後的死亡。[85]
金斯伯格一生吸煙,儘管他曾因健康和宗教原因嘗試戒煙,但晚年繁忙的日程安排讓他難以戒煙,最終他又開始吸煙。
20世紀70年代,金斯伯格兩次輕微中風,最初被診斷為貝爾氏麻痹症,導致他嚴重癱瘓,一側面部肌肉出現類似中風的下垂。晚年,他還經常患高血壓等小病。這些癥狀很多都與壓力有關,但他從未放慢腳步。
艾倫·金斯堡,1979年
金斯堡憑藉《美國的隕落》(與艾德里安·里奇合著的《潛入沉船》)榮獲1974年美國國家圖書獎。
1986年,金斯堡在馬其頓斯特魯加國際詩歌節上榮獲金花環獎,他是繼W. H.奧登之後第二位獲此殊榮的美國詩人。在斯特魯加,金斯堡會見了其他金花環獎得主布拉特·奧庫賈瓦和安德烈·沃茲涅先斯基。
1989年,金斯堡出演了羅莎·馮·普勞恩海姆執導的獲獎影片《沉默=死亡》,該片講述了紐約市同性戀藝術家為爭取艾滋病教育和艾滋病毒感染者權利而進行的抗爭。[87]
1993年,法國文化部長授予金斯伯格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
金斯伯格繼續儘力幫助他的朋友:他自掏腰包給赫伯特·亨克(Herbert Huncke)捐款,定期給鄰居亞瑟·羅素(Arthur Russell)提供延長線,供他家用錄音設備供電[88][89],並娶了身無分文、吸毒成癮的哈里·史密斯(Harry Smith)。
除了1997年2月20日在紐約大學詩歌朗誦會上作為特別嘉賓亮相外,金斯伯格於1996年12月16日在舊金山的「書匠書店」(The Booksmith)舉行了被認為是他最後一次的朗誦會。
金斯伯格因充血性心力衰竭住院治療,但未獲成功。最後一次出院回家后,他繼續打電話與通訊錄里的幾乎所有人告別。有些電話里充滿了悲傷,甚至被哭聲打斷,而另一些電話里則充滿了喜悅和樂觀。[90]金斯伯格在病危期間繼續寫作,他的最後一首詩《我不會做的事(懷舊)》寫於3月30日。
1997年4月5日,他在曼哈頓東村的閣樓中逝世,在親朋好友的陪伴下,終年70歲,因肝炎併發症罹患肝癌去世。[19] 格雷戈里·科索、羅伊·利希滕斯坦、帕蒂·史密斯等人紛紛前來弔唁。[92] 他的遺體被火化,骨灰安葬在紐瓦克戈梅利·切塞德公墓的家族墓地中。[93] 奧洛夫斯基為他默哀。
1998年5月14日,聖約翰大教堂舉行了一場悼念活動,約2500名金斯伯格的朋友和粉絲出席。[94][95][96]
1998年8月,包括卡特菲什·麥克達里斯在內的多位作家在金斯伯格的農場舉行了一場集會,以紀念艾倫和「垮掉的一代」。[97]
《心靈捕手》(1997年12月上映)是獻給金斯伯格和四個月後去世的巴勒斯的。[98]
社會和政治活動
言論自由
金斯伯格樂於談論禁忌話題,這使他在保守的20世紀50年代成為一個頗具爭議的人物,並在20世紀60年代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沒有一家信譽良好的出版社會考慮出版《嚎叫》。當時,《嚎叫》中使用的這種「性話題」被一些人認為是粗俗的,甚至是色情的,可能會被依法起訴。[45] 金斯伯格在詩中使用了諸如「口交者」、「被干屁股」和「屄」等詞語來描繪美國文化的不同方面。當時,許多討論性的書籍都被禁,包括《查泰萊夫人的情人》。[45]金斯伯格所描述的性並非異性戀已婚夫婦之間的性行為,甚至並非長期戀人之間的性行為。相反,金斯伯格描繪的是隨意的性行為。[45] 例如,在《嚎叫》中,金斯伯格讚揚了一位「讓百萬少女心動不已」的男人。金斯伯格使用了粗獷的描述和露骨的性語言,指出這位男人「飢腸轆轆、孤獨地在休斯頓閑逛,尋找爵士樂、性愛或湯」。金斯伯格還在詩歌中探討了當時禁忌的同性戀話題。《嚎叫》中充斥的露骨性語言最終引發了一場關於第一修正案的重要審判。金斯伯格的出版商因出版色情作品而被起訴,最終法官以這首詩具有「救贖的社會意義」為由,公開駁回了指控[99],從而開創了一個重要的法律先例。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金斯伯格繼續探討爭議性話題。從1970年到1996年,金斯伯格長期與美國筆會中心合作,致力於捍衛言論自由。在解釋他如何處理爭議性話題時,他經常提到赫伯特·亨克:他說,20世紀40年代,當他第一次認識亨克時,金斯伯格發現亨克因海洛因成癮而病入膏肓,但當時海洛因是一個禁忌話題,亨克無處求助。[100]
在越南戰爭抗議活動中的作用
在1972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抗議
金斯伯格是反戰宣言《抵制非法權威的呼籲》的簽署人之一,該宣言由激進知識分子團體「抵抗」的成員於1967年在反徵兵者中傳播。其他簽名者和「抵抗」組織成員包括米切爾·古德曼、亨利·布勞恩、丹尼斯·萊弗托夫、諾姆·喬姆斯基、威廉·斯隆·科芬、德懷特·麥克唐納、羅伯特·洛厄爾和諾曼·梅勒。[101][102] 1968年,金斯伯格簽署了「作家和編輯戰爭稅抗議」誓言,誓言拒絕納稅以抗議越南戰爭。[103] 後來,他成為「戰爭稅抵抗」項目的發起人,該項目實踐並倡導將稅收抵抗作為一種反戰抗議的形式。[104]
他親臨湯普金斯廣場公園騷亂當晚(1988年),並向《紐約時報》提供了目擊證詞。[105]
與共產主義的關係
在紅色恐慌和麥卡錫主義肆虐的年代,金斯伯格公開談論他與共產主義的聯繫,以及他對昔日共產主義英雄和勞工運動的欽佩。我欽佩菲德爾·卡斯特羅以及許多其他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人物。[106][107]金斯伯格是古巴公平競爭委員會的成員。[108]在《美國》(1956年)一書中,金斯伯格寫道:「美國,我小時候曾是一名共產主義者,我並不後悔。」 傳記作家喬納·拉斯金聲稱,儘管金斯伯格經常強烈反對共產主義正統觀念,但他持有「自己獨特的共產主義觀點」。政府或任何暴力政府……我必須說,我所觀察到的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武裝政府與暴力政府之間幾乎沒有區別」。[110]
金斯伯格曾前往多個共產主義國家推廣言論自由。他聲稱,中國等共產主義國家歡迎他,因為他們認為他是資本主義的敵人,但當他們將他視為麻煩製造者時,往往會轉而反對他。例如,1965年,金斯伯格因公開抗議對同性戀者的迫害而被古巴驅逐出境。[111] 古巴人將他送往捷克斯洛伐克。在被命名為「五月之王」(Král majálesu,[112] 一個學生節日,慶祝春天和學生生活)一周后,金斯伯格因涉嫌吸毒和公共場合醉酒而被捕,安全機構StB沒收了他的幾件作品,他們認為這些作品淫穢且道德敗壞。金斯伯格隨後於5月7日被驅逐出捷克斯洛伐克。 1965年,[111][113] 受德國國家安全局(StB)命令。[114] 瓦茨拉夫·哈維爾指出,金斯伯格是他重要的靈感來源。[115]
同性戀權利
金斯伯格最重要且最具爭議的貢獻之一是他對同性戀的公開態度。金斯伯格是同性戀自由的早期倡導者。1943年,他發現自己內心深處「堆積如山的同性戀傾向」。他在詩歌中公開而生動地表達了這種渴望。[116] 他還在其《名人錄》中將終身伴侶彼得·奧洛夫斯基列為配偶,以此為同性婚姻的標誌。後來的同性戀作家將他對同性戀的坦誠討論視為一個開端,讓他們可以更公開、更誠實地談論一些以前常常只是暗示或用比喻來提及的事情。[100]
通過對性進行生動細緻的描寫,以及頻繁使用被視為不雅的語言,他挑戰了——並最終改變了——淫穢法。[引文] [需要引用] 他堅定地支持那些挑戰淫穢法的言論人士(例如威廉·S·巴勒斯和倫尼·布魯斯)。
北美男童戀童癖協會 (NAMBLA) 會員
金斯伯格是北美男童戀童癖協會 (NAMBLA) 的支持者和會員,該協會是美國一個戀童癖和戀童癖倡導組織,致力於廢除法定同意年齡法,並使成人與兒童之間的性關係合法化。[117][需要引用] 金斯伯格表示,他加入該組織是為了「捍衛言論自由」,[118] 他表示:「對 NAMBLA 的攻擊散發著政治惡臭、為利益而進行的迫害、缺乏幽默感、虛榮、憤怒和無知……我加入 NAMBLA 是因為我也愛男孩——每個有點人性的人都愛男孩。」[119] 1994 年,金斯伯格出演了一部關於 NAMBLA 的紀錄片,名為《雞鷹:愛男孩的男人》(播放於 NAMBLA 網站)。艾倫在一次演講中朗讀了一首「獻給青春的生動頌歌」(他用男同性戀俚語「chickenhawk」來表達)。[117] 他朗讀了一首詩《甜心男孩,給我你的屁股》(Sweet Boy, Gimme Yr Ass),出自他所著的《心靈呼吸》(Mind Breaths)[120]。這本詩集被他稱為「戀童癖狂想曲」,其中生動地描繪了與男孩發生性關係的場景。[121]
安德里亞·德沃金在她2002年出版的《心碎》(Heartbreak)一書中聲稱,金斯伯格與北美男童戀協會(NAMBLA)結盟別有用心:
1982年,各大報紙以大標題報道最高法院裁定兒童色情製品非法。我當時非常激動。我知道艾倫不會激動。我當時確實以為他是個公民自由主義者。但事實上,他是個戀童癖者。他加入北美男童戀協會並非出於某種瘋狂而抽象的信念,認為該協會的聲音必須被聽到。我是認真的。以下是艾倫直接對我說的話:並非源於我的推斷。他對自己與兒童發生性關係的權利極其強硬,並且不斷追求未成年男孩。[122]
金斯伯格在談及他曾經的好友德沃金時說道[123]:
我從安德里亞學生時代就認識她了。有一次我跟她說,我年輕時有過很多婚外情,對象都是16、17、18歲的人。我說:「你打算怎麼辦?把我送進監獄嗎?」 她說:「你應該槍斃你。」 問題是,她年輕時遭受過性騷擾,至今仍未從創傷中恢復過來,現在她把這種情緒發泄在普通的戀人身上。[124]
娛樂性毒品
艾倫·金斯伯格、蒂莫西·利里和約翰·C·利利,攝於1991年
金斯伯格經常談論吸毒問題。他組織了「大麻合法化運動」(LeMar)的紐約市分會。[125]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他積極致力於揭開LSD的神秘面紗,並與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共同致力於推廣LSD的普及使用。數十年來,他一直倡導大麻合法化,同時在其著作《放下你的香煙》(Put Down Your Cigarette Rag,別吸煙)中警示讀者警惕煙草的危害:「別吸煙,別吸煙,尼古丁,尼古丁,別吸煙 ...除了與麥考伊合作之外,金斯伯格還就此事親自與 20 世紀 70 年代的中央情報局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對質,但赫爾姆斯否認中央情報局與販賣非法毒品有任何關係。[127][129] 金斯伯格撰寫了許多散文和文章,研究和收集中央情報局涉嫌參與販毒的證據,但直到 1972 年麥考伊出版了他的書,人們才開始認真對待他。[127] 1978 年,金斯伯格收到《紐約時報》主編的一封信,為沒有認真對待他的指控而道歉。[130] 他的歌曲/詩歌《CIA Dope calypso》探討了政治話題。美國國務院回應麥考伊最初的指控,稱他們「無法找到任何證據證實這些指控,更不用說確鑿的證據了」。[131] 隨後,美國中央情報局監察長[132]、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133]和美國參議院情報活動政府行動研究特別委員會(又稱丘奇委員會[134])的調查也認定這些指控毫無根據。
作品
金斯伯格早期的詩歌大多採用押韻的正式格律,這與他的父親以及他的偶像威廉·布萊克的風格相似。他對傑克·凱魯亞克作品的欽佩促使他更加認真地對待詩歌。1955年,在一位精神病醫生的建議下,金斯伯格退出了工作,將畢生精力投入到詩歌創作中。[135]不久之後,他創作了《嚎叫》。這首詩使他和「垮掉的一代」的同輩們獲得了全國性的關注,並讓他得以以職業詩人的身份度過餘生。晚年,金斯伯格進入學術界,自1986年起直至去世,一直擔任布魯克林學院的傑出英語教授,教授詩歌。[136]
朋友的啟發
金斯伯格一生都聲稱,他最大的靈感來自凱魯亞克的「自發散文」概念。他認為文學應該發自靈魂,不受意識的限制。金斯伯格比凱魯亞克更容易修改。例如,當凱魯亞克看到《嚎叫》的初稿時,他很不喜歡金斯伯格用鉛筆進行的編輯性修改(例如,在第一行中將「黑色」和「憤怒」調換位置)。凱魯亞克只是在金斯伯格的堅持下才寫下了他的自發散文概念,因為金斯伯格想學習如何將這種技巧運用到他的詩歌中。[22]
《嚎叫》的靈感源自金斯堡的朋友卡爾·所羅門,《嚎叫》正是獻給他的。所羅門是一位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愛好者(他把金斯堡介紹給了阿爾托),他患有臨床抑鬱症。所羅門曾想自殺,但他認為符合達達主義的自殺方式是去精神病院要求進行腦白質切除術。精神病院拒絕了,並給他提供了多種治療方案,包括電擊療法。《嚎叫》第一部分的最後部分很大程度上描述了這種情況。
他還強調,摩洛克在多個方面都是人類的一部分,因為決定反抗社會構建的控制系統——從而對抗摩洛克——是一種自我毀滅。金斯堡在《嚎叫》中提到的許多角色,例如尼爾·卡薩迪和赫伯特·亨克,都因濫用藥物或放蕩不羈的生活方式而自我毀滅。《嚎叫》的個人層面或許與政治層面同樣重要。卡爾·所羅門,一個因反抗社會而毀滅的「最優秀頭腦」的典型例子,與金斯堡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母親息息相關:「終於和母親做愛了」這句台詞出現在關於卡爾·所羅門的長篇章節之後,而在第三部分中,金斯堡說道:「我和你一起在羅克蘭,你模仿著我母親的影子。」金斯堡後來承認,創作《嚎叫》的動力源於對病弱母親的同情,而當時他還沒有準備好直接面對這個問題。他直接以1959年的《卡迪什》(Kaddish)[22]來探討這個問題。該詩在天主教工人周五晚會上首次公開朗讀,可能是因為與托馬斯·默頓的聯繫。[138]
導師和偶像的啟發
金斯伯格的詩歌深受現代主義(最重要的是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開創的美國現代主義風格)、浪漫主義(特別是威廉·布萊克和約翰·濟慈)、爵士樂的節奏和韻律(特別是查理·帕克等波普音樂家的節奏)以及他自身的噶舉派佛教修行和猶太背景的影響。他認為自己繼承了英國詩人兼藝術家威廉·布萊克、美國詩人沃爾特·惠特曼和西班牙詩人費德里科·加西亞·洛爾迦傳承下來的富有遠見的詩歌風格。金斯伯格詩歌的力量、探索性的專註力、悠長而輕快的詩行,以及新世界的活力,都與他所宣稱的靈感源源不斷相呼應。[22][100][115]
他與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通信,後者當時正在創作關於他家附近工業城市的史詩《帕特森》。在參加了威廉姆斯的朗誦會後,金斯伯格寄給了這位老詩人幾首詩,並寫了一封介紹信。這些早期詩歌大多押韻、有韻律,並使用了像「你」這樣的古體代詞。威廉姆斯不喜歡這些詩,並告訴金斯伯格:「在這種模式下,完美是基本的,而這些詩並不完美。」[22][100][115]
儘管威廉姆斯不喜歡這些早期詩歌,但他喜歡金斯伯格信中那種活力四射的風格。我已將這封信收錄在《帕特森》的後半部分。他鼓勵金斯伯格不要效仿古代大師,而是要用自己的聲音和普通美國人的聲音說話。從威廉姆斯那裡,金斯伯格學會了專註於強烈的視覺形象,這與威廉姆斯自己的座右銘「唯有物,無所求」相符。學習威廉姆斯的風格,使他從早期的形式主義作品轉向了鬆散、口語化的自由詩體。早期突破性的詩歌包括《砌磚工的午餐時間》和《夢境記錄》。[22][115]
卡爾·所羅門向金斯伯格介紹了安東尼·阿爾托(《結束上帝的審判》和《梵高:被社會自殺的人》)和讓·熱內(《花之聖母》)的作品。菲利普·拉曼蒂亞向他介紹了其他超現實主義者,超現實主義持續對他產生影響(例如,《卡迪什》的部分內容就受到了安德烈·布勒東《自由聯盟》的啟發)。金斯伯格聲稱,《嚎叫》和其他詩歌中重複的重複運用受到了克里斯托弗·斯馬特在其詩歌《歡騰的一天》等作品中的啟發。金斯伯格還聲稱自己受到了其他更傳統的影響,例如:弗朗茨·卡夫卡、赫爾曼·梅爾維爾、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埃德加·愛倫·坡和艾米莉·狄金森。[22][100]
金斯伯格還對俳句和保羅·塞尚的繪畫進行了深入研究,並從中汲取了一個對他的作品至關重要的概念,他稱之為「眼球踢」。我在觀看塞尚的畫作時注意到,當眼睛從一種顏色移到另一種對比色時,眼睛會痙攣,或者說「踢」。同樣,我發現,兩種看似對立的事物之間的對比也是俳句的一個常見特徵。金斯伯格在他的詩歌中運用了這種技巧,將兩個截然不同的意象組合在一起:弱者與強者,高雅文化的產物與低俗文化的產物,神聖與邪惡。金斯伯格最常用的例子是「氫氣點唱機」(後來成為菲利普·格拉斯創作的一首循環歌曲的標題,歌詞取自金斯伯格的詩歌)。另一個例子是金斯伯格在鮑勃·迪倫1966年緊張刺激的電吉他巡演中對迪倫的評價。迪倫在安非他命[139]、鴉片[140]、酒精[141]和迷幻藥[142]的混合作用下,像個服用了右旋安非他命的小丑。「眼球踢」和「氫氣點唱機」這兩個短語都出現在《嚎叫》中,還有一句塞尚的原話:「永恆的上帝之父」。[100]
音樂的靈感
另見:《純真與經驗之歌》(艾倫·金斯堡專輯)
艾倫·金斯堡也從音樂中汲取靈感。他經常在詩歌中融入音樂,總是用一架古老的印度簧風琴創作旋律,並在朗誦時演奏。[143] 他為威廉·布萊克的《純真之歌》和《經驗之歌》創作並錄製了伴奏音樂。他還錄製了其他幾張專輯。為了創作《嚎叫》和《威奇托漩渦經》,他與極簡主義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合作。
金斯堡曾與鮑勃·迪倫、衝撞樂隊、帕蒂·史密斯[144]、菲爾·奧克斯和富格斯樂隊[51]等藝術家合作,從他們身上汲取靈感,並激勵他們。他與迪倫合作過各種項目,並保持了多年的友誼。[145]
1981年,金斯堡錄製了一首名為《鳥腦》的歌曲。他由「膠子樂隊」(The Gluons)伴奏,這首歌作為單曲發行。[146] 1996年,他與保羅·麥卡特尼和菲利普·格拉斯共同創作了歌曲《骷髏之歌》(The Ballad of the Skeletons),[147] 這首歌在當年的Triple J Hottest 100單曲榜上排名第八。
風格與技巧
通過學習他的偶像和導師,以及從朋友那裡獲得靈感——更不用說他自己的實驗——金斯伯格發展出了一種很容易被認定為金斯伯格式的個人風格。[148] 金斯伯格表示,惠特曼的長詩是一種動態技巧,很少有其他詩人敢於進一步發展,惠特曼也經常被拿來與金斯伯格比較,因為他們的詩歌都對男性體態進行了性感化處理。[22][100][115]
金斯伯格早期的許多長詩實驗都包含某種形式的首語重複,即重複一個「固定基調」(例如《嚎叫》中的「誰」,《美國》中的「美國」),這已成為金斯伯格風格的一個顯著特徵。[149] 他後來表示,這只是一種依靠,因為他缺乏信心;他還不相信「自由飛翔」。[150] 20世紀60年代,在《卡迪什》的某些部分(例如「嘎嘎叫」)使用了首語重複之後,他基本上放棄了首語重複的形式。「後期節拍」鮑勃·迪倫以使用首語重複而聞名,例如在《糾結於藍色》中,每節詩結尾都用這個短語代替了副歌。[100][115]
他早期對詩歌格式方法的幾次實驗,成為他後期詩歌風格的常規元素。在《嚎叫》的初稿中,每一行都採用了「階梯式三行詩」的格式,讓人聯想到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151]。他在創作長詩時放棄了「階梯式三行詩」,儘管階梯式詩後來出現,尤其是在《美國的淪陷》的遊記中。[需要引證] 可以說,他最重要的兩首詩《嚎叫》和《卡迪什》都採用了倒金字塔的結構,大段大段地銜接小段。在《美國》中,他也嘗試過長短詩的混合。[100][115]
金斯伯格成熟的風格運用了許多特定且高度發達的技巧,這些技巧體現在他在那洛巴教法中使用的「詩意口號」中。其中最突出的是他未經編輯的心理聯想,以揭示思維活動(「第一個想法,最好的想法。」「心靈是形狀,思想是形狀。」)。他更喜歡通過仔細觀察的物理細節來表達,而不是抽象的陳述(「展示,不要講述。」「除了事物之外,別無想法。」)[152] 在這些作品中,他繼承並發展了現代主義寫作的傳統,這種傳統在凱魯亞克和惠特曼的作品中也有體現。
在《嚎叫》和其他詩歌中,金斯伯格從19世紀美國詩人沃爾特·惠特曼的史詩般的自由詩風格中汲取靈感。[153] 兩人都熱情洋溢地描寫了美國民主的承諾(和背叛)、情色體驗的核心重要性以及對日常生活真理的精神追求。《耶魯評論》編輯J. D. 麥克拉奇稱金斯伯格是「他那一代最著名的美國詩人,既是一股社會力量,也是一種文學現象。」麥克拉奇補充道,金斯伯格和惠特曼一樣,「是一位老派的吟遊詩人——氣勢恢宏,充滿黑暗的預言,一部分是熱情洋溢,一部分是祈禱,一部分是咆哮。他的作品最終是我們這個時代心靈的歷史,充滿了各種矛盾的衝動。」麥克拉奇的諷刺悼詞界定了金斯伯格(「一位垮掉的一代詩人,他的作品……通過將回收天才與慷慨的模仿同理心相結合而產生的新聞主義,以引起讀者共鳴;總是充滿抒情,有時甚至充滿詩意」)和凱魯亞克(「一位才華橫溢的詩人,『垮掉的一代』中最耀眼的明星,他後來成為流行文化的象徵……[儘管]實際上他遠遠超過了他的同時代人……凱魯亞克是一位獨具匠心的天才,探索然後回答——就像一個世紀前的蘭波一樣,是出於必然而非選擇——真實的自我表達的要求適用於美國唯一一位文學大師不斷發展的靈動心靈……」)。
榮譽
他的詩集《美國的隕落》榮獲1974年美國國家圖書獎詩歌類獎項。[14]
金斯伯格憑藉《美國的隕落》(與艾德里安·里奇的《潛入沉船》合著)榮獲1974年美國國家圖書獎。[14]
1979年,他榮獲美國國家藝術俱樂部金獎,併入選美國藝術與文學學院。[15]
1986年,金斯伯格榮獲馬其頓斯特魯加國際詩歌節金花環獎,成為繼W. H. 奧登之後第二位獲此殊榮的美國詩人。在斯特魯加,金斯伯格會見了其他金花環獎得主布拉特·奧庫賈瓦和安德烈·沃茲涅先斯基。
1989年,金斯伯格出演了羅莎·馮·普勞恩海姆執導的獲獎影片《沉默=死亡》,該片講述了紐約市同性戀藝術家為爭取艾滋病教育和艾滋病毒感染者權利而展開的抗爭。[87]
1993年,法國文化部長授予金斯伯格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1995年,金斯伯格憑藉其著作《大都會問候:1986-1992年的詩歌》入圍普利策獎決賽。[16] 1993年,他被哥倫比亞出版社追授約翰·傑伊獎。[154][155]
2014年,金斯伯格成為「彩虹榮譽步行」的首批獲獎者之一。「彩虹榮譽步行」是舊金山卡斯特羅街區的一項星光大道,旨在表彰「在其領域做出重大貢獻」的LGBTQ人士。[156][157][158]
參考書目
《嚎叫及其他詩歌》(1956年),ISBN 978-0-87286-017-9
《卡迪什及其他詩歌》(1961年),ISBN 978-0-87286-019-3
《空鏡:早期詩歌》(1961年),ISBN 978-0-87091-030-2
《現實三明治》(1963年),ISBN 978-0-87286-021-6
《雅格書信》(1963年)——與威廉·S·巴勒斯合著
《星球新聞》(1968年),ISBN 978-0-87286-020-9
《印度期刊》(1970年),ISBN 0-8021-3475-0
《早期布魯斯:1971-1974年的拉格斯、民謠與簧風琴歌曲》(1975年),ISBN 0-916190-05-6
《憤怒之門:1948-1951年的押韻詩》(1972年),ISBN 978-0-912516-01-1
《美國的衰落:這些州的詩歌》(1973年),ISBN 978-0-87286-063-6
《鐵馬》(1973年)
艾倫·金斯堡的《逐字逐句:關於詩歌、政治與意識的講座》(1974年),戈登·鮑爾編輯,ISBN 0-07-023285-7
《悲傷塵埃的榮耀:夏日林中工作時所作的詩》(1975)
《心靈呼吸》(1978),ISBN 978-0-87286-092-6
《冥王頌歌:1977-1980 年詩歌》(1981),ISBN 978-0-87286-125-1
《1947-1980 年詩集》(1984),ISBN 978-0-06-015341-0。 2006年,重新出版,並添加了後來的材料,名為《詩集1947-1997》,紐約,哈珀柯林斯出版社
《白色裹屍布詩集:1980-1985》(1986年),ISBN 978-0-06-091429-5
《大都會問候詩集:1986-1993》(1994年)
《嚎叫註釋》(1995年)
《光輝詩集》(1996年)
《詩選:1947-1995》(1996年)
《死亡與名望:1993-1997年的詩歌》(1999年)
《深思熟慮的散文:1952-1995》(2000年)
《嚎叫及其他詩歌》五十周年紀念版(2006年),ISBN 978-0-06-113745-7
《殉道與詭計之書:1937-1952 年的早期日記與詩歌》(達卡波出版社,2006 年)
《艾倫·金斯堡與加里·斯奈德書信選》(Counterpoint 出版社,2009 年)
《我在此致敬偉大的事業之初:勞倫斯·費林蓋蒂與艾倫·金斯堡書信選,1955-1997 年》(城市之光出版社,2015 年)
《我這一代最優秀的思想:垮掉一代文學史》(格羅夫出版社,2017 年)
To Frank O』Hara
Sometimes when my eyes are red
I go up on top of the RCA Building
and gaze at my world, Manhattan—
my buildings, streets I』ve done feats in,
lofts, beds, coldwater flats
—on Fifth Ave below which I also bear in mind,
its ant cars, little yellow taxis, men
walking the size of specks of wool—
Panorama of the bridges, sunrise over Brooklyn machine,
sun go down over New Jersey where I was born
& Paterson where I played with ants—
my later loves on 15th Street,
my greater loves of Lower East Side,
my once fabulous amours in the Bronx
faraway—
paths crossing in these hidden streets,
my history summed up, my absences
and ecstasies in Harlem—
—sun shining down on all I own
in one eyeblink to the horizon
in my last eternity—
matter is water.
Sad,
I take the elevator and go
down, pondering,
and walk on the pavements staring into all man』s
plateglass, faces,
questioning after who loves,
and stop, bemused
in front of an automobile shopwindow
standing lost in calm thought,
traffic moving up & down 5th Avenue blocks behind me
waiting for a moment when ...
Time to go home & cook supper & listen to
the romantic war news on the radio
... all movement stops
& I walk in the timeless sadness of existence,
tenderness flowing thru the buildings,
my fingertips touching reality』s face,
my own face streaked with tears in the mirror
of some window—at dusk—
where I have no desire—
for bonbons—or to own the dresses or Japanese
lampshades of intellection—
Confused by the spectacle around me,
Man struggling up the street
with packages, newspapers,
ties, beautiful suits
toward his desire
Man, woman, streaming over the pavements
red lights clocking hurried watches &
movements at the curb—
And all these streets leading
so crosswise, honking, lengthily,
by avenues
stalked by high buildings or crusted into slums
thru such halting traffic
screaming cars and engines
so painfully to this
countryside, this graveyard
this stillness
on deathbed or mountain
once seen
never regained or desired
in the mind to come
where all Manhattan that I』ve seen must disappear.



/cloudfront-us-east-1.images.arcpublishing.com/pmn/6G73VQNI45DK7AJHO3TVN7AYAE.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