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答聶文蔚》 [2017/04]
- 奧巴馬致女友:我每天都和男人做愛 [2023/11]
- 愛國者的喜訊,干吃福利的綠卡族回國希望大增 [2017/01]
- 周五落軌的真的是個華女 [2017/03]
- 現場! 全副武裝的警察突入燕郊 [2017/12]
- 法拉盛的「雞街」剛剛又鬧出人命 [2017/11]
- 大部分人品太差了--- 中國公園裡的「黃昏戀」 [2019/12]
- 亞裔男孩再讓美國瘋狂 [2018/09]
- 年三十工作/小媳婦好嗎 /土撥鼠真屌/美華素質高? [2019/02]
- 看這些入籍美加的中國人在這裡的醜態百出下場可期 [2019/11]
- 黑暗時代的明燈 [2017/01]
- 文革宣傳畫名作選之 「群醜圖」 都畫了誰? [2024/01]
- 當今的美國是不是還從根本上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 [2017/10]
- 香港的抗爭再次告訴世人 [2019/06]
- 中國女歡呼日本地震 歐洲老公驚呆上網反思 [2024/01]
- 加入外國籍,你還是不是中國人?談多數華人的愚昧和少數華人的覺醒 [2018/02]
- 周末逛法拉盛,還是坐地鐵? [2017/10]
- 春蠶到死絲方斷, 丹心未酬血已干 [2017/03]
《讀書》
幽沉謝世事,俯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縹帙各舒散,前後互相逾。瘴痾擾靈府,日與往昔殊。臨文乍了了,徹卷兀若無。竟夕誰與言,但與竹素俱。倦極更倒卧,熟寐乃一蘇。欠伸展肢體,吟詠心自愉。得意適其適,非願為世儒。道盡即閉口,蕭散捐囚拘。巧者為我拙,智者為我愚。書史足自悅,安用勤與劬。貴爾六尺軀,勿為名所驅 。(柳宗元)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閑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柳宗元)
《漁翁》
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岩上無心雲相逐。(柳宗元)
柳宗元公,不僅是文學家,而且也是哲學家。在中國思想史上,大概應該說是絕無僅有的。
毛澤東特別喜歡柳宗元的文章,常常在與人談話中大加讚賞,如稱柳宗元既是文學家,也是唯物論者;稱自屈原《天問》以來,幾千年間只有柳宗元《天對》這一篇。毛澤東的文章喜歡廣徵博引,當中有不少柳宗元的大段文章。毛澤東還喜歡柳宗元的詩歌,常在作品上圈閱以示嘉許,並多次書寫以表欣賞之情。更帶有戲劇性的是,由曾當過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國民政府文學院院長、新中國中央文史館館長的章士釗編撰的百萬字巨著《柳文指南》,竟然得以在「橫掃封資修」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版,這當中還受到當時掌管意識形態生殺大權的康生的刁難。究其原因,是毛澤東對柳宗元的極力推崇,而《柳文指南》是亘古未有的研究柳宗元的鴻篇巨製,毛澤東明確支持並親自審稿。
(都都的博客:《尋幽訪古柳侯祠》)
《黔之驢》
柳宗元曾經描寫過的「黔驢之技」,也是一個很好的教訓。一個龐然大物的驢子跑進貴州去了,貴州的小老虎見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後來,大驢子還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們八路軍新四軍是孫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辦法對付這個日本妖精或日本驢子的。目前我們須得變一變,把我們的身體變得小些,但是變得更加紮實些,我們就會變成無敵的了。
(《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1942年9月7日],《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三卷,第863頁)
《黔之驢》是柳宗元寫的《三戒》中的一篇。另外兩篇是《臨江之麋》、《永某氏之鼠》,均為諷刺性寓言小品文。作者在《三戒》序言中說:「吾恆惡世之人,不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強怒,竊時以肆暴,然卒迨於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黔之驢》所諷刺的,便是「出技以強怒」。後人對它的解釋,是認為沒有真本領的人,常常捉襟見肘,陷入濫竽充數的尷尬。黔驢技窮,遂成為有名的成語。
毛澤東談《黔之驢》的發揮,自是另有一格。他從大與小的角度來說明,小的只要「更加紮實些」,便能戰勝「龐然大物」,猶如小老虎能吃掉沒有本領的大驢子一樣。
(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一個很好的教訓(讀柳宗元〈黔之驢〉)》,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
柳宗元曾寫過諷刺性寓言小品文《三戒》,《黔之驢》就是其中的一篇,還有兩篇是《臨江之麋》、《永某氏之鼠》。這些文章都是針對現實生活的問題,高度抽象、概括、形象化的力作,有強烈的政治思想內容和現實主義精神,經世不衰,獨具風格。在《黔之驢》中,柳宗元通過描寫一頭外強中乾的驢子,終於被老虎吃掉的故事,諷刺了「乘物以逞」、「出技以強怒」, 「竊時以肆暴」,「然卒迨於禍」的人。後人將此歸納為「黔驢之技」或「黔驢技窮」,用以比喻本領有限,或比喻有限的一點本領全使出來了,再沒有別的辦法了。
毛澤東在1942年9月7日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借用這個寓言,來說明敵人是不可怕的,儘管外表是個龐然大物。毛澤東把八路軍比作「貴州小老虎」,把日本帝國主義比作貌似強大的「驢子」,目的在於告訴人們,不管敵人外表如何龐大,由於它的本質是外強中乾的,只要我們對付得法,它最終是要被精壯的革命力量所消滅。
同一年,毛澤東在魯藝作報告時,又引用了這個寓言,不過這回的目的是為了教育從這裡出去工作的幹部,不要擺知識分子的架子,自認為是「洋包子」,而瞧不起本地的「土包子」幹部,要和本地幹部加強團結,和群眾打成一片。
1942年5月30日,毛澤東到魯迅藝術學院講話時,他號召魯藝學員不要只局限於小魯藝,還要到「大魯藝」去開展工作。毛澤東說:「你們快畢業了,將要離開魯藝了。你們現在學習的地方是小魯藝,還有一個大魯藝。只是在小魯藝學習還不夠,還要到大魯藝去學習。大魯藝就是工農兵群眾的生活和鬥爭。廣大的勞動人民就是大魯藝的教師。你們應當認真地向他們學習,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點逐步移到工農兵這一邊來,才能成為真正的革命文藝工作者。農民的腳踩過牛屎,但卻比知識分子乾淨。」「你們從小魯藝到大魯藝去,就是外來幹部。不要瞧不起本地的幹部,不要以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土包子。知識分子不要擺知識架子。」為了更好地說明這個道理,毛澤東又講了《黔之驢》的故事。他說:「貴州沒有驢勾子(驢勾子是陝北農村的毛驢的稱呼。毛澤東講話常用人民口頭的語言),有人運了一匹驢勾子到那裡去。它到那裡就是外來的洋包子。貴州的老虎個子不大,是個本地的土包子。小老虎看見驢勾子那種龐然大物的樣子,很害怕。驢勾子叫了一聲,小老虎嚇壞了,就逃得遠遠的。後來久了一點,小老虎覺得驢勾子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就走近它,並且碰碰它。驢勾子大怒,用腳踢了小老虎一下,小老虎這才看出它那兩下子,就說,『原來你不過就這點本事!』結果小老虎就吃掉了這匹驢勾子。」毛澤東在講這個故事時,一邊講,一邊裝作老虎觀察和偵察驢勾子的樣子,走向旁邊正在作記錄的同志,大家都笑了。
(劉修鐵編著:《毛澤東妙評古詩書鑒賞》 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
《天對》
主席認為柳宗元的文章的思想性比較韓愈的高,不過文章難讀一些。他指出:屈原寫過《天問》,過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寫《天對》,膽子很大。我問主席能否說柳宗元是唯物主義者?他說頂多能說有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成分。主席很推崇劉禹錫,「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頭前萬木春」這兩句詩他就很欣賞。主席對歷史實在熟,說到這兩句時,立即說出來這首詩是劉禹錫送白居易的。劉禹錫的文章不多,但他所作《天論》三篇,主張「天與人交相勝」之說,他的反對迷信,反對因果報應的思想,主席給以較高的評價。我問主席,劉禹錫可否算是唐朝的一個樸素唯物主義者?主席說:「可以。」主席對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的評價都與我們想的不同,他都同我們作了具體分析。
(毛澤東1965年6月20日在上海同劉大傑的談話,見《毛澤東在上海》第143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版)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義哲學家,見之於他的《天論》,這篇哲學論著提出了「天與人交相勝」的論點,反對天命論。劉禹錫發展了這種唯物主義,而這篇文章無一語談到這一大問題,是個缺點。
(林克:《在毛澤東身邊的歲月片段》,見《緬懷毛澤東》下冊第56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天問》了不起,幾千年以前,提出各種問題,關於宇宙、關於自然,關於歷史。
(毛澤東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的談話)
(柳宗元:《天對》[摘錄])
「本始之茫,誕者傳焉。
鴻靈幽紛,曷可言焉!
往來屯屯,龐昧革化,
惟元氣存,而何為焉!」
「位庸庇民,仁克蒞之。
紂淫以害,師殛圮之。」
(屈原:《天問》[摘錄])
「遂古之初,誰傳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誰能極之?
馮翼惟象,何以識之?
明明暗暗,惟時何為?」
「授殷天下,其德安施?
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作為進步的政治家和詩人,屈原以其獨特的藝術想象和批判精神,在《天問》中提出了170多個疑問,內容涉及天地的形成和結構,以及人類社會變遷的種種神話傳說,諸如伏羲為帝,女媧造人,殷受天命等等既成的傳說和信念,屈原都表示了大膽的懷疑和駁難,體現了神話不可依,天命不可待的歷史理性觀念。故魯迅說屈原的《天問》「懷疑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瑣末,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
《天對》是柳宗元被謫貶永州(今湖南零陵)期間寫的論著,它以逐段回答《天問》的形式,批判地繼承了《天問》的思想,發展了苟況的「天人相分」的唯物主義觀點和王充等人的「元氣一元論」的唯物主義學說,並吸收了當時自然科學的成果,批駁了各種把自然界神化的傳說和神靈創世的謬論。作者認為:在天地未形成以前,宇宙間只存在著一種叫做「元氣」的原始物質;宇宙是無限的;天地萬物是由宇宙間陰陽兩種元氣的變化產生的。這些觀點,不但堅持了唯物論,而且包含著樸素的辯證法因素,對推進我國古代唯物主義的宇宙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此外。作者還運用無神論去解釋歷史。駁斥了「君權神授」的謬說,指出人心向背是決定王朝興廢的主要原因,這在當時也是有積極意義的。
《天問》既是一篇氣勢磅礴的文學作品,又是一篇表達歷史理性思維的哲學論著,把二者結合起來,屈原是第一個。故引起思想家而兼詩人的毛澤東的重視。《天問》的「了不起」,在於它提出了問題;《天對》的了不起,則在於它以唯物主義思想和詩的形式回答了問題,而且《天問》產生以來,就這麼一篇有膽識的「對」,這是毛澤東格外推崇柳宗元的地方。
毛澤東認為,要全面準確地評論柳宗元的文學創作的積極意義,就不能拋開他在唯物主義思想方面的突出貢獻。《光明日報》1959年3月1日刊載了一位文學史家寫的讀書札記《柳宗元的詩》,簡要分析了柳宗元的政治諷喻、反映民生疾苦、抒發個人牢騷、離鄉去國的悲愁幾類題材的作品。毛澤東讀後,對工作人員談了自己的看法:「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義哲學家,見之於他的《天說》,劉禹錫發展了這種唯物主義;而這篇文章無一語談到這一大問題,是個缺點。」我們在前面引的那段話,工作人員在回憶中說到柳宗元的《天論》,提出「天與人交相勝」的觀點,可能是誤記。提出這個觀點的是劉禹錫的《天論》,但柳宗元是贊成這個觀點的。柳宗元在讀到劉禹錫的《天論》后,曾寫了《答劉禹錫的〈天論〉書》,說剛讀時,「大喜,謂有以開吾志慮」。在這篇文章,他便引了劉的天人「交勝」之說。
劉禹錫寫《天論》,則是起因於柳宗元的另一篇文章,叫《天說》。劉的意思是要欲畢《天說》未究之言。《天說》是柳宗元在永州時寫的一篇短文,是同韓愈就天有無意志問題進行論戰的。韓愈認為天有意志,能賞功罰禍。柳宗元在這篇文章中說,天地、元氣、陰陽都是物質,沒有意志,人類社會是「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毛澤東對這篇文章很熟悉。1963年5月在杭州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的一次談話中說:「柳宗元30歲到40歲有10年都在永州,他的山水散文,與韓愈論辯的文章,就是在永州寫的。」
毛澤東說「劉禹錫發展了這種唯物主義」,是指劉禹錫的《天論》(上、中、下)。《天論》是劉禹錫的哲學思想的代表作,主要論述了天的物質性、天與人的關係、產生天命論的根源三大問題。柳宗元的《天說》只闡明了天人相異的觀點,劉禹錫的《天論》3篇則進一步提出了「天非務勝乎人」,而「人誠務勝乎天」的觀點,所以說是「發展了」柳宗元的唯物主義。
劉大傑在《一次不平常的會見》這篇文章中還記敘,毛澤東1965年6月20日同他的談話中,還從天命觀說到王安石。劉大傑說:對於宋朝的王安石,我們一向總以為他能反對天命、反對封建宗法是他的進步之處。主席卻認為,在王安石之前已經有人提出過反對天命、反對封建宗法的思想,譬如屈原、王充。主席說:王安石最可貴之處在於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在神宗皇帝時代,他搞變法,當時很多人攻擊他,他不害怕。封建社會不比今天,輿論可以殺人,他能挺得住,這一點不容易做到。。。。。。。主席還說:「要學習王安石這種『人言不足恤』的精神,不要害怕批評,要敢於發展、堅持自己的見解。」
毛澤東由此及彼地閱讀和評論《天問》、《天對》、《天說》、《天論》以及王安石的「人言不足恤」的觀點,足見其讀書方法之一斑,也說明他對古代哲學中「天人關係」這一課題的重視。
(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了不起的唯物主義(讀屈原〈天問〉、柳宗元〈天對〉、〈天說〉、劉禹錫〈天論〉)》,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
《柳文指要》
《給康生(1)的信》
(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
康生同志:
章士釗(2)先生所著《柳文指要》(3)上、下兩部,22本。約百萬言,無事時可續續看去,頗有新又引人入勝之處大抵揚柳(4)抑韓(5),翻二王、八司馬(6)之冤案,這是不錯的。又辟桐城(7)而頌陽湖(8),譏帖括而尊古文,亦有可取之處。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觀,於文、史、哲諸方面仍止於以作者觀點解柳(此書可謂《解柳全書》),他日可能引起歷史學家用唯物史觀對此書作批判。如有此舉,亦是好事。此點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預作精神準備,也不要求85齡之老先生改變他的世界觀。
毛澤東1965年8月5日
(根據手稿刊印)
[註釋]
(1)康生,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
(2)章士釗,字行嚴,當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
(3)《柳文指要》是一部對柳宗元文集的專門性研究著作。
(4)柳,指柳宗元,唐朝文學家、哲學家。
(5)韓,指韓愈,唐朝文學家、哲學家。
(6)二王,指王叔文、王伾。王叔文在唐順宗時任翰林學士,聯合王伾等人進行政治改革。改革失敗后,王叔文被殺,王伾遭貶。八司馬,指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陳諫、凌准、程異、韋執誼。他們支持唐順宗進行政治改革,失敗后八人均被貶為遠僻地方的司馬,故有八司馬之稱。
(7)桐城,指桐城派,清朝散文流派。由康熙時方苞開創,其後,劉大魁(左偏旁為木)、姚鼐等又進一步加以發展。他們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名。他們主張學習《左傳》、《史記》等先秦兩漢散文和唐宋古文家韓愈、歐陽修等人的作品,講究「義法」,要求語言「雅潔」。
(8)陽湖,指陽湖派,清朝散文流派。由惲敬、張惠言等開創。惲為江蘇陽湖(今武進)人,後繼者亦多同縣人,故名。他們源於桐城派,但對桐城派古文的清規戒律有所不滿,作文取法儒家經典,而又參以諸子百家之書。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430-431頁]》)
章士釗(1882-1973),湖南長沙人,字行衍,又字行嚴。清末任上海《蘇報》主筆,宣傳革命派主張。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北京農業學校校長、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司法總長等。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從1960年開始著手撰寫專門研究柳宗元文集的著作《柳文指要》,到1965年完成初稿,達100萬字。全書分上下兩部。上部是「體要之部」,照柳宗元原文編次,逐篇加以探討,包括評論、考證、校箋等幾個方面;下部「通要之部」,按專題分類論述有關柳宗元和柳文的各項問題,如政治、文學、儒佛、韓柳關係等等。作者對柳宗元進行了長期的研究,引用了大量的材料,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書中對唐朝永貞政變作了評價,充分肯定了二王、八司馬的政治主張。作者從各方面論證了柳宗元在歷史上的進步性,特別是在韓柳的對比中,竭力褒揚了柳宗元「以民為主」的思想,駁斥了韓愈「以民為仇」的謬論。全書對柳文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都作了詳盡分析,並對有關的論著,一一加以介紹和評論,為柳宗元的研究提供了不少線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稱之為「解柳全書」。
文學史上,韓柳並稱,但二人的思想卻是對立的。毛澤東推崇柳宗元,在相當的程度上是因為他是歷代詩文作家中不多見的具有唯物主義思想和進步的歷史理論建樹的人,而且還是中唐掀動政壇風波的王叔文政治集團中的核心人物。毛澤東得知章士釗在撰寫《柳文指要》后,便說自己也愛讀柳問,請章士釗將書稿送他先睹為快。1965年6月,章士釗先後把100萬字的初稿給毛澤東送去,毛收到后,派人給章士釗送去桃杏各五斤,並附上一信:
「行嚴先生:
大作收到,義正詞嚴,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納為盼!投報相反,尚乞諒解。含之同志身體如何?附此向她問好,望她努力奮鬥,有所益進。
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毛澤東逐字逐句地讀了《柳文指要》,並親自修改了若干處。「義正詞嚴,敬服之至。」這是毛澤東的初步評價,到了7月中旬,毛澤東已把《柳文指要》上、下兩部通讀一遍。於是,他又寫信給章士釗,談有關《柳文指要》的事。
「行嚴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經讀過一遍,還想讀一遍。上部也還想再讀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讀。大問題是唯物史觀問題,即主要是階級鬥爭問題。但此事不能求只於世界觀已經固定之老先生們,故不必改動。嗣後歷史學者可能批評你這一點,請你要有精神準備,不怕人家批評。。。。。。。(馬注;查《毛澤東書信選》,此處所刪節之原文為:又高先生評郭文已讀過,他的論點是地下不可能發掘出真、行、草墓石。草書不會會書碑,可以斷言。至於真、行是否曾經書碑,尚待地下發掘證實。但爭論是應該有的,我當勸說郭老、康生、伯達諸同志贊成高二適一文公諸於世。)柳文上部,盼即寄來。
敬頌
康吉!
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信中「指要」、「柳文」,都是指《柳文指要》。這裡指出了這部書稿的根本缺陷。信中所說「友人」,是指康生。康生當時是分管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毛澤東再次索要他已經讀完歸還的《柳文指要》上部,也是為了把上、下兩部一併送給康生看。
8月5日,毛澤東把全書送給康生時附了我們在前面摘引的那封信,除重申了「大問題是唯物史觀問題」這一缺陷外,著重肯定了《柳文指要》的優點。這年12月,康生讀完該書稿,給毛澤東寫了封信,說:「。。。。。。85歲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萬巨著,實非易事。我讀完之後,覺得主席8月5日信中對此書的評價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確的。此書翻永貞政變之案,申二王八司馬之冤,揚柳子厚『以民為主』的思想,斥韓退之『以民為仇』的謬論,確有新鮮引人入勝之處。此書也有缺點,如著者不能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去解釋柳文,對柳宗元這個歷史人物缺乏階級分析,對社會進化,以為『承新仍返諸舊』,『新舊如環,因成進化必然之理』等等。」最後說:「對於一個沒有研究馬列主義的人,這是可以理解的。」顯然,這些評論,都是學毛澤東的,並無康生自己的觀點。
接到康生的信后,毛澤東於1966年1月12日把書稿退還給章士釗,還附上一信。他寫道:「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經讀完交來,茲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見,是否妥當,請酌定。」在信尾,毛澤東又加一個附註說:「附件兩紙,另康生同志來信一件,均附上。又及。」毛澤東把康生的信原封不動連帶信封一起轉給章士釗,信封原是康生寫給毛澤東的,上書:「請交毛主席 康生寄」。毛澤東把「主席」二字勾去,親筆在旁邊寫上「章行嚴先生閱」,這必是康生始所未料的。因為康生一拖再拖,本意是不願該書出版的。
本來,到此一切問題算解決了,《柳文指要》終於可以問世了。但剛剛送到中華書局,「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在那摧毀一切舊文化的混亂年月中,章士釗或許是感到自己的著述與當時的氣氛不協調,於1966年5月10日給毛澤東寫了封信,信中說:「我今天看到《中國青年報》說:我們一定不放過鄧拓這一夥,一定不放過一切牛鬼蛇神,《工人日報》亦如是雲。於斯世也,天下執筆之士,不能以我與鄧拓原不相識,強自寬解,而須將自己之一字一句嚴行琢磨,是否未廁於一切牛鬼蛇神之列。」正是從這一心悸難測的情境出發,章士釗在這封信中對自己的《柳文指要》進行了自我批評。他說:「我的所謂指要,純乎按照柳子厚觀點,對本宣科,顯然為一個封建社會的文藝殭屍塗脂抹粉。。。。。。。這一類著作,投在今日蓬勃發展的新社會中,必然促使進步奮發的農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體無完膚。」這個檢討,自然是根據當時的大批判氣氛,強化了毛澤東在1965年7月18日給章士釗信中所指出的缺陷。其強化之辭未始沒有違背本意的因素。
毛澤東對《柳文指要》的態度,是一貫的。並不因「文革」的開始而加以改變。他在章士釗信中有關自我檢討的幾句話旁邊批註道:「此話說得過分」,「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掛著共產主義羊頭,賣反共狗肉的壞人,而不是並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點,不是『痛加』」,「何至如此」等等。這或許從一個側面反映,毛澤東當時首肯的意識形態的大批判,主要是針對「黨內走資派」的,確實是學術問題,且又是黨外民主人士的著作,他的態度是較為冷靜的。
章士釗在信末說,請主席給他三年時間,補習不可不讀的馬列著作和《毛澤東選集》,然後將其《柳文指要》一書重行訂正,再付梓印行。對此,毛澤東批示,將此信送到劉少奇、周恩來閱,給康生閱,再與章士釗先生一商。又說,《柳文指要》一是照原計劃出版,一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時間,加以修改,然後印行。毛澤東寫這個批示的時間,是1966年5月17日,也就是發布「5·16通知」,標誌「文革」開始的第二天。
很可能是由於康生的意見,或者是由於當時急速發展、變化多端的形勢,《柳文指要》的出版與否,不可能提上日程。反正是擱下來了。本來,在那樣的日子裡,出版一本缺少唯物史觀來研究老古董的著作,是難以想象的。
當「文革」的狂暴逐漸減弱,轉為「斗、批、改」的時候,章士釗又重新提出了《柳文指要》的出版問題。此時大約是1970年,本來毛澤東已批准同意出版,中華書局也已排版,但此時的康生已竊取中央要位,見《柳文指要》最後要出版了,他橫生枝節,提出要作者改變觀點,將全書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重新修改一遍,才能出版。章士釗得知康生意見后,寫了一封措辭激烈的長信給毛澤東並康生,斷然拒絕按康生意見修改全書。可惜,這封信已找不到,章士釗女兒章含之有殘存半截草稿,從草稿中可見其當時心情十分激動,修改處墨跡極淡,顯然是墨未研就就下筆了。信的草稿中說:「根據康生的意見,看來原作不加改動斷不可,即為社會必須掃除的穢濁物,哪裡還談得上出版。」又嘲諷地說:「夫唯物主義無他,只不過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之高貴讀物。」還說,「我未信人類有不可變更的觀點,亦未聞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為此請求主席恕我違抗指揮之罪(章旁註:指不改變原稿),並賜我三年期限補習必不可不讀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選,如果天假之年能達九十六闕比時,諒已通將《指要》殘本重新訂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眾,不望無瑕,庶乎少過。我之此一請求出於十分真誠。臨紙無任惶恐。待命之至,未肅順致崇祺。康生副委員長均此未另。」
這封信,使《柳文指要》於1972年9月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共14冊。這自然是毛澤東促成的結果,他批轉康生等研究處理,康生等騎虎難下,只好做個順水人情。1971年8月14日章士釗以90歲高齡續寫該書《通要之部續序》時,喟然嘆曰:「柳文重發光艷,殆起於1949年之大革命初期,倘無毛主席著作發揚,決不會有崇柳風尚。」
《柳文指要》之出版,自是波折起伏。但毛澤東對這部鴻篇巨製的興趣之大,閱讀之細,評論之中肯,則是值得稱道的。他讀一遍后說還要再讀一遍。還認真把書稿中的錯別字改掉,提出一些具體的修改意見。1966年3月,章士釗以86歲高齡撰寫《柳文指要》跋時,便有「上部繕就,以示一二友人,猥蒙檢閱一過,除指點要義,並改正錯誤外,猶承說明序言引何義門訊朱竹坨輯《明詩綜》例之未得其正,負責述作,無須自貶到怕人笑破口云云,吾謹受教。。。。。。」之語。足見毛澤東在該書上所花的功夫。從一般的文學史研究角度而言,他認為這部著作寫得不錯,「義正詞嚴」,觀點「頗有新意和引人發聵之外」,「可謂解柳全書」。具體說來,毛澤東推重的是該書「揚柳抑韓,翻二王、八司馬之冤案,這是不錯的。又辟桐城而頌陽湖,譏帖括而尊古義,亦有可取之處」。這些,體現了毛澤東對柳宗元及其相關的文學現象、政治現象,與章士釗相通的評價傾向。
褒貶一種歷史文化現象,事實上有不同的角度和標準;取一致評論傾向,不一定表示不同的評論者有相同的歷史觀和思想方法。當毛澤東用自己的觀點來分析柳宗元及其相關的文化現象時,他深感《柳文指要》的「大問題是唯物史觀問題」,即「作者不懂唯物史觀,於文史哲諸方面仍止於以作者觀點解柳」。不可能做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解釋柳文,因而在具體論證時缺乏對柳宗元這一歷史人物的階級分析,過分誇大了他在歷史上的進步性。對此,毛澤東並不企望章先生一下子改變他的世界觀。同時明確告訴作者:「嗣後歷史學者可能批評你這一點,請你要有精神準備,不怕人家批評。」章士釗也深感自己的著作會有不足之處,在全書的總序里表示,當世碩學,如有所匡正,得以讀易補過,「何時獲知,當即力事補正」。(本條目諸多事實材料引自章含之回憶文章)
(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頗有新義,可謂解柳全書(讀章士釗〈柳文指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
大言小言,各適其域。工也,農也,商也,學也,兵也,其中多數人,皆能參與文事之列。經濟有變化,反映經濟之政教亦將有變化,文事亦將有變化。一成不變之事,將不可能。
(毛澤東1965年8月讀章士釗《柳文指要·跋》手稿的批改。見喬東光《毛澤東與〈邏輯指要〉、〈柳文指要〉》,《瞭望》1985年第52期)
毛澤東認為,《柳文指要》缺少唯物史觀,作者在該書跋文中所論韓柳倡導的明白曉暢的古文運動之興起與貢獻,即可視為一例。(馬註:章士釗在《柳文指要·跋》手稿中的原文如下:「存其利而去其害,即不啻表顯文化進步之正當規律,從而人心翕習,童叟無違,事有固然,毫不足怪。此一新興文運,上同象魏之懸,下無宗派之爭,雍容揄揚,行見永遠相持於不蔽。斯誠游夏神遊於文學之表,所莫贊一辭,而是迥然別開一新紀元,以與古文相行而特顯其長,即不多論。」)在書中其他地方,作者進而提出「承新仍返諸舊」,「新舊如環,因或進化必然之理」的歷史循環觀點。基於次,作者一方面提出古文運動乃一「新興文運」,「別開一新紀元」,但又認為它是「存其利而去其害」,乃傳統古文之「事有固然」。毛澤東似乎不滿足於這種囿於文學形式本身的存廢因循來評價古文運動,特意刪掉其中「永遠相持於不蔽」幾字,加寫了前面引述的這段話,這就把評價的重心,放到文學與經濟、政治,文學與一般大眾的關係上面。從這一個側面反映了毛澤東經濟、政治決定文化的歷史主義觀點。
(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文事隨經濟、政教而變化(讀章士釗〈柳文指要·跋〉)》,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
《呈郭老》
《五絕·呈郭老(1)》
(一九七三年)
郭老從柳退,
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產黨,
崇拜孔二先(2)。
[註釋]
(1)此詩出處及寫作背景介紹見《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注一。
《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注一:
《封建論》:柳宗元(773-819)撰。文章通過對古代社會的分封制度的細緻分析,嚴厲抨擊了封建藩鎮的割據局面,以及士族大夫的「世食祿邑」和由此產生的「不肖居上,賢者居下」的不合理現象。認為,社會制度是不以任何人或少數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它在「勢」的支配下,就是聖人也無力興廢。從根本上否定了「人生有命,富貴在天」的傳統思想。文章以史實說明了秦代開創的郡縣制較封建制的優越性,批駁了一些人企圖恢復分封制「與三代比隆」的倒退思想。這篇著名的政論文在歷史上的地位,用蘇軾的話來概括,即「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秦不封建論》)
郭老:郭沫若(1892-1978),四川樂山人。中國現代著名的文學家、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和社會活動家。這首詩見之於王年一《大動亂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陳晉《毛澤東與文藝傳統》、高凱、於伶主編《毛澤東大觀》及馮錫剛《雲水蒼茫未得殊——郭沫若在「文革」後期》等著述。有關論著介紹此詩寫作背景說:1968年10月在八屆二中全會閉幕會上,毛澤東直率地說:我這個人有點偏向,不那麼喜歡孔夫子。贊成說他代表奴隸主、舊貴族的觀點,不贊成說他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因此郭老的《十批判書》崇儒反法,我也不那麼贊成。。。。。。。1973年春,毛澤東就寫了一首反對郭沫若「崇拜孔二先」的小詩。7月4日同王洪文等談話時又提到郭老在《十批判書》里自稱人本主義,孔夫子也是人本主義,不能大罵秦始皇。8月5日,毛澤東給江青念了《讀〈封建論〉——呈郭老》一詩以後,又說:「歷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會前期有建樹的,都是法家。這些人主張法治,犯了法就殺頭,主張厚今薄古。儒家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都是主張厚古薄今。」
(2)孔二先:孔二先生的略稱。
(慶振軒、閻軍編著:《毛澤東詩詞全集輯注》 甘肅文化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
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
(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
「勸君少罵秦始皇,
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秦猶在,
孔學名高實秕康。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
莫從子厚返文王。」
這首詩根據作者審定的鉛印件刊印。近年來此詩不少出版物所載,多有訛誤。
[註釋]
[《封建論》] 唐代文學家、思想家柳宗元的史論文章,闡發了設置郡縣、廢除分封、加強中央集權、反對藩鎮割據的主張。
[莫從子厚返文王]子厚,即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東解(今山西運城縣解州鎮)人。文王,即周文王,姓姬名昌,周末為西伯,周族領袖,晚年自號為文王。周文王時開始推行較完備的封建制(即分封制)。本句是說不要從柳宗元的反對分封回到周文王的實行分封制,即反對倒退。
說《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 是毛澤東所作,有確鑿的檔案可以證明。(一)這首詩編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時,是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鉛印件刊印的。(二)1973年8月7日周恩來曾寫給毛澤東一封親筆信,信中說:「江青同志在昨晚政治局會議上已將主席讀柳子厚的封建論和呈郭老的詩以及有關問題給我們傳達了,我們也議論了一下。」毛澤東圈閱了這封信,這表明,毛澤東認同了「呈郭老的詩」是他寫的。周恩來的這封親筆信保存在中央檔案館。
(《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主編:吳正裕,副主編:李捷、陳晉。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
詩以《讀〈封建論〉呈郭老》為題,可知是由讀柳宗元《封建論》一文有感而發,就儒法問題向郭老呈詩商榷。
柳宗元的《封建論》精闢地分析了「封建制」之大弊,「郡縣制」之大利,指出「郡縣制」是保證中央集權、國家統一、長治久安的政治體制。毛澤東高度評價《封建論》的意義,力勸郭老「熟讀」之,可謂慧眼獨具,語切心長。
尾聯「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以誠懇友善的語氣,寫出對郭老的期望,勸說郭老多讀一些唐人柳宗元所寫的《封建論》這篇文章,不要從柳宗元的正確觀點倒退到周文王的「封建制」時代去。。。。。。。此聯作結,哲理深刻,發人深思。
全詩主旨,在於批評郭老崇儒反法的錯誤觀點,勸說他正確認識和對待秦始皇這樣一位有重大功績和深遠影響的歷史人物。
1973年8月5日,毛澤東對江青念出這首後來題為《讀〈封建論〉呈郭老》的七律,要她當場手記。毛澤東之所以要呈詩郭沫若,主要是由於他不同意郭老在研究政治思想史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揚儒抑法的傾向,《十批判書》是其代表性言論,因而以詩提出批評探討意見。
毛澤東作此詩,還有其直接的政治原因。1971年林彪事件之後,在林彪住處查出一些肯定孔儒言論(如「克己復禮」 之類)的條幅和材料。林彪之子林立國搞的反革命政變計劃《「571工程」紀要》,又徑直把毛澤東比為秦始皇而加以咒罵。毛澤東便越發感到林彪的極右實質與孔儒思想有必然的聯繫,批林必須批孔。因而呈詩郭老,就《十批判書》尊孔和罵秦始皇的問題提出批評商榷。在念了呈郭老一詩后,毛澤東還說:「郭老對待秦始皇,對待孔子那種態度和林彪一樣。」
郭沫若在重慶時期寫的《十批判書》,在《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一文中,把秦始皇當作「站在奴隸主的立場」,使「已解放了的人民,又整個化為了奴隸」,從而把社會向後扭轉的人物加以否定,而稱讚孔子「是順應著當時的社會變革潮流的」,「企圖建立一個新的體系以為新來的封建社會的韌帶」。對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則沿襲歷史偏見,看成是專制暴行。毛澤東不同意郭的觀點。他曾明確表示:「我這個人比較有點傾向,就不那麼高興孔夫子。看了說孔夫子是代表奴隸主、舊貴族,我偏向這一方面,而不贊成孔夫子是代表那個時候新興地主階級。因此,我跟郭老在這一點上不那麼對。你那個《十批判書》崇儒反法,我也不那麼贊成。」又說:「我贊成郭老的歷史分期,奴隸制以春秋戰國之間為界。但是不能大罵秦始皇。」
毛澤東從小讀孔夫子的書,但「不那麼高興孔夫子」,而「贊成秦始皇」。「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他反孔的態度就比較鮮明。但從延安時期到50年代,他都多次說過:「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孔夫子當然是有地位的」,「此人不可一筆抹殺」。60年代中期以後,毛澤東對孔子越來越反感,對秦始皇的功績越來越稱讚。他說過:「在中國歷史上,真正做了點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說空話。幾千年來,形式上是孔夫子,實際上是按秦始皇辦事。」「孔夫子有些好處,但也不是很好。我們應該講句公道話。秦始皇比孔子偉大得多。」
毛澤東曾說:「秦始皇是第一個把中國統一起來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統一中國,而且統一了中國的文字、中國的各種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後來一直沿用下來。中國過去的封建君主還沒有第二個超過他的。」
(龔國基:《爽直的批評 誠的規勸——〈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賞析》,見《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主編:吳正裕,副主編:李捷、陳晉。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
(2011)
中華書局近日再版章士釗先生《柳文指要》,該書是20世紀70年代在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親自關懷下得以出版的名著。關於此書出版過程及其價值,中華書局前副總編輯程毅中先生曾撰一文,詳加闡述。今節選此文,與讀者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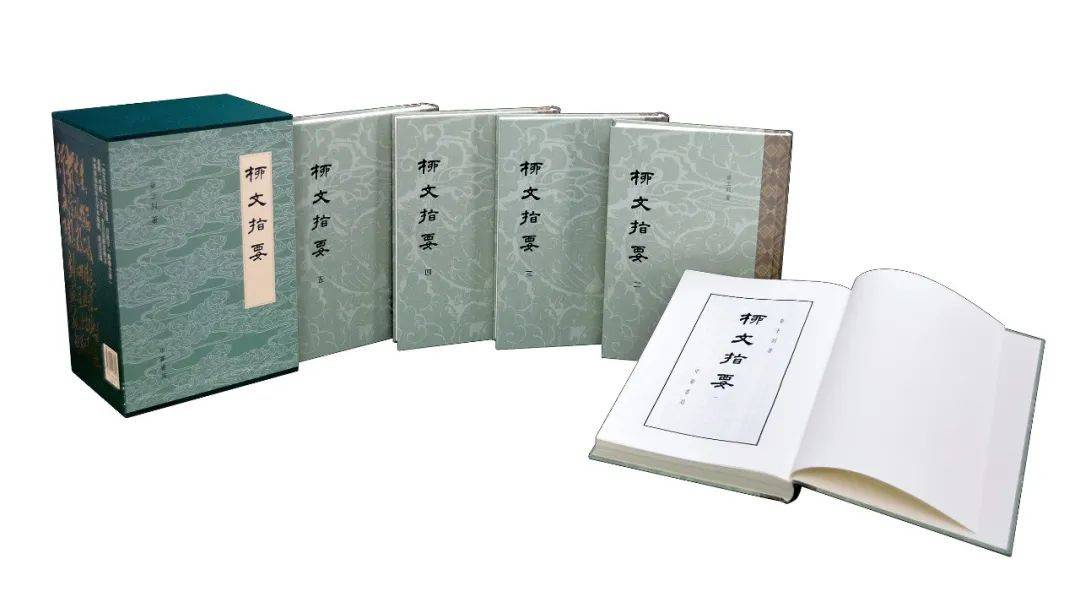
毛主席在1965年7月18日寫信給章士釗,說: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經讀過一遍,還想讀一遍。上部也還想再讀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讀。大問題是唯物史觀問題,即主要是階級鬥爭問題。但此事不能求之於世界觀已經固定之老先生們,故不必改動。嗣後歷史學者可能批評你這一點,請你要有精神準備,不怕人家批評。……《柳文》上部盼即寄來。
《柳文指要》在「文化大革命」中間出版,引起了很大的震動。這是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為落實政策、恢復出版工作、重新貫徹雙百方針的一項措施,章士釗的這部書稿正好提供了一個絕好的典型。《柳文指要》是一部研究柳宗元文學和思想的學術著作,它存在一些觀點問題,即毛澤東指出的缺乏唯物史觀的大問題,然而這些都是學術思想問題,世界觀的問題。儘管歷史學者可能會批評這一點,但可以照樣出版。由毛澤東主席親自抓的這一個典型,本來是可以推動一下出版工作的。可惜是不久又被「四人幫」策劃的「批林批孔」運動衝擊了。
《柳文指要》是章士釗先生長期研究柳宗元文集的專著。他六十多年鍥而不捨,積累了大量的資料,對柳文作了全面的研究。全書分上下兩部,上部為「體要之部」,按柳集原文編次逐篇加以探討;下部為「通要之部」,按專題分篇論述有關柳宗元和柳文的各項問題。

章士釗
我們說他對柳文作了全面的研究,概括說來,就是從義理、考據、文章三個方面都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首先從文章說起,《指要》頭一篇《平淮夷雅》的敘論就說:「子厚行文,講求運用虛字,虛字不中律令,即文無是處,此讀《答杜溫夫書》,即可見到。」接著就列舉了《平淮夷雅》文中的若干虛詞,一一加以詮釋,主要是訓詁學的論述。最後說:「右不過於柳文首篇,擇若干關鍵字,略加詮釋云爾。綜舉全集,子厚大抵每篇皆在細針密縷之中,加意熨貼,從無隨意塗抹,泥沙俱下之病,必須明了此義,方可得到柳文之神。退之稱子厚之文,雄深雅健,所謂雅者,不窺破此竅,即不能了解何謂之雅。」《指要》書中,對柳文所作訓詁學和修辭學的詮釋,隨處可見,足見作者的真知灼見。作者不僅是古文的評論者,而且自己就是一個古體散文的作家,正如他在本書總序開頭所說:
余少時愛好柳文,而並無師承,止於隨意閱讀,稍長,擔簦受學於外,亦即挈柳集自隨,逮入仕亦如之,此集隨余流轉,前後亘六七十年,為問余所得幾許?余頗艱於自斷。要之餘平生行文,並不摹擬柳州形式,獨柳州求文之潔,酷好公谷,又文中所用助字,一一葉於律令,依事著文,期於不溢,一掃昌黎文無的標、泥沙俱下之病。余遵而習之,漸形自然,假令此號為有得,而余所得不過如是。
章士釗先生酷愛柳文,自己又是長期用柳文的那種文體來寫文章,自然能夠深刻地體會到柳文的語言特色和修辭藝術。按照他的研究,就是寫文章用虛字要精確,行文要雅潔。我們今天一般地不必再學寫這種古體的文言文了,然而要想讀懂和透徹理解古書的內容,還是需要多讀、熟讀一些古代的文章。在這方面,《指要》還是能給我們一些幫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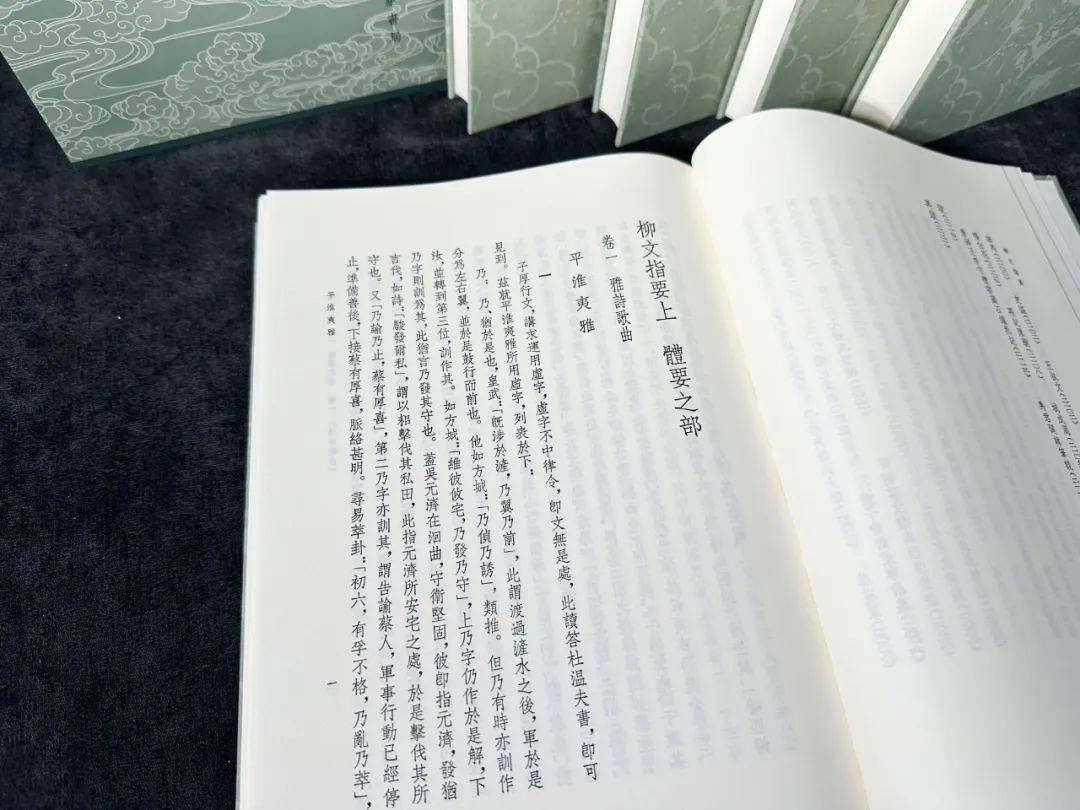
其次,《指要》在考據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發現。如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石背先友記》的敘論中,對柳宗元父親柳鎮的朋友,努力考證其生平行事,在前人註釋的基礎上繼續搜羅材料,又有不少補充。例如袁滋的事迹,就引用了《劇談錄》和《逸史》的記載(中華書局1971年版397~399頁,以下引書均據此版);又在通要之部里列了《補記袁滋》一條(2011~2016頁),引用雲南昭通豆沙關的摩崖石刻,上面有袁滋的題字,也可據以考證袁滋出使南詔的行程。又如《晉文公問守原議》一篇的論述,揭示了「永貞逆案」的隱秘,作者採用卞孝萱先生的考證,論定《續幽怪錄》(原名《續玄怪錄》,宋朝人避始祖趙玄朗諱改「玄」作「幽」)中的《辛公平上仙》條,實為記載順宗被弒之資料。《辛公平上仙》是一篇小說,用影射的手法反映了順宗被害的宮廷政變。在此之前,陳寅恪先生曾有《〈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一文,指出《辛公平上仙》「假道家『兵解』之詞,以紀憲宗被弒之實」。但沒有注意到《續幽怪錄》中有篡改年號的情況(宋人刻書時因避仁宗趙禎諱改「貞元」作「元和」),結論未達一間。《指要》則採取了實為憲宗之父唐順宗李誦被弒的新解,就更為精密了。通要之部卷十四又列了《再記續幽怪錄》一條(2033~2034頁),對《辛公平上仙》的文字還作了校勘,也可見作者不斷積累資料之勤奮。
最後,再從義理方面說,《指要》非常注重理論探討,這是它的鮮明特色。這集中體現於通要之部的序。序言第一段論述永貞政變的始末,歸納為十三條,提綱挈領,表達了對永貞革新的高度評價。從而肯定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和文學成就,如第十一條所說:「永貞政變之全幀形象,不論表裡明暗,皆在子厚慧心炯目之中,特於全集之文字間,僅從夾縫中窺測一二,無緣獲得正面佐證,吾之號為指要,所指無過爾爾。」第十三條又說:
永貞逆案之一名詞,不見於有唐各項公私著錄,千餘年來,舉世幾無人了解到此一無名之商臣,應與元和聖德融成一詞。於是子厚不得不以春秋之筆,在晉文問守原一史跡上,提出許世子止、趙盾二例,以討伐羞當時陷後代之亂臣賊子。
作者正是從唐順宗被弒的新證,提出了「永貞逆案」的結論,把「永貞政變」的「內禪」疑案坐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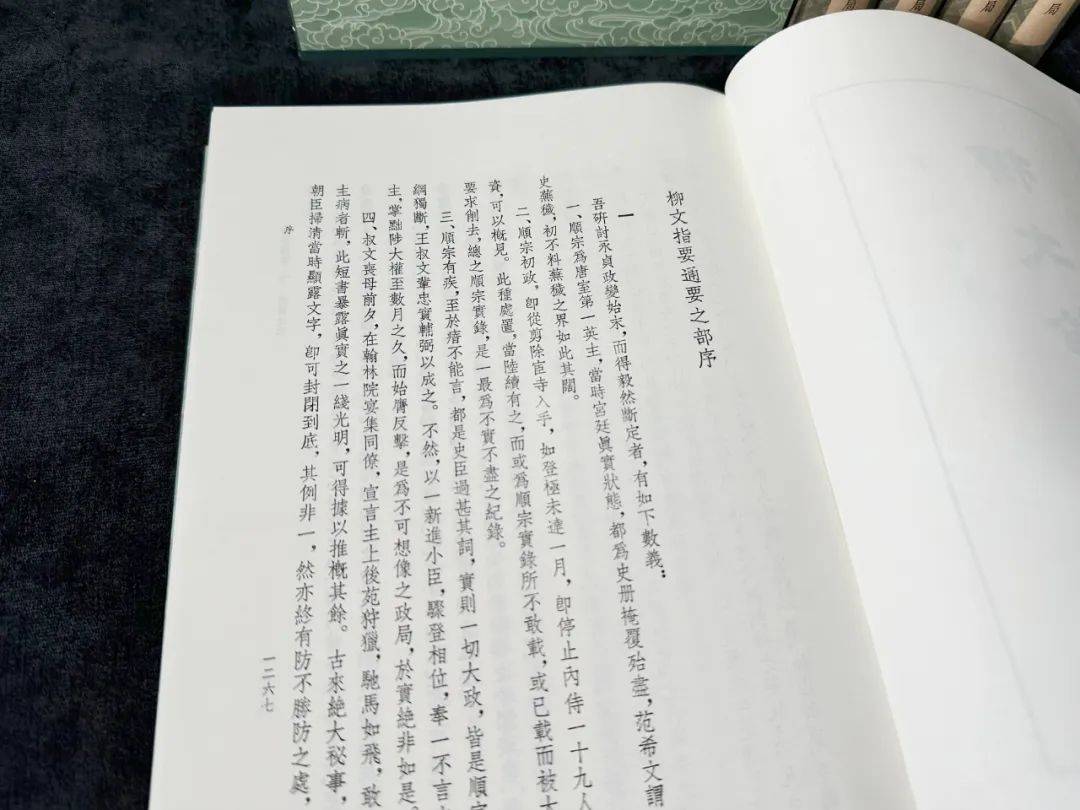
第二段對柳宗元的政治抱負,歸納為十條,如第五條所說:
集中之眎民詩,是其政略之全部圖形。士實蕩蕩,農實董董,工實蒙蒙,賈實融融,四民先使安居而樂業,國家於焉相應扶助,使之各盡其力,以廣食用而利遷作。
著者在柳集中,抓住了《眎民詩》中的「帝視民情」、「帝情民視」及《貞符》中的「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等名言,加以發揮,充分闡揚了柳宗元的民主思想和樸素唯物主義觀點。書中反覆強調了柳宗元的政治思想是「以民為主」,而與之齊名的韓愈則是「以民為仇」,形成了尖銳的對比。雖然已有人指出,《指要》對柳宗元還缺乏階級分析,根本問題是著者還不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者,然而我們也要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待古人和章士釗先生。在歷史研究上,如果能夠揭示史實的真相,哪怕是比較接近客觀事實的現象,那就是歷史唯物論得以發揮作用的一個基點。柳宗元不可能是一個徹底的唯物論者,更不可能是一個真正依靠人民的革命者,但是他作品中所表現的進步思想,在歷史上無疑應予充分肯定。正因為還沒有得到多數人的認同,所以《指要》要大聲疾呼地為之爭辯,特別在「永貞革新」事件的評價上,要把柳宗元與韓愈作尖銳的對比。這一點我們是首先應該理解的。
序言的第三段,對柳宗元的學養,也歸納了十一條。雖然講的是文學上的成就,然而也不能不涉及思想基礎。如第三條說:「子厚主張文以明道,與退之無異致,但強調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因而生平不打妄語,文皆本色,此足以自信,而兼取信於後世。此一詣也,退之根本達不到。」又如第十一條說:
民為邦本,古今一致,子厚主旨一定,推概於古,即使古為今用。以三國而論,曹魏與民接近,而漢久與民絕,故不當卑視曹魏。集中舜禹之事一文,應視作推重民主之大文字,為正統論立定基礎,他人不敢如此下筆,何偽之有?
著者對古為今用特別重視,即認定柳宗元有古為今用的做法(如《舜禹之事》中肯定曹魏能得民心),更在柳宗元的研究中竭力發揮了古為今用的意圖。《指要》在論述中往往聯繫現實,乃至借古喻今,觀點十分鮮明。如卷十九《敵戒》的論述,引用1966年2月20日《人民日報》觀察家評論的例證,即引用《敵戒》的話來反擊帝國主義。同卷《三戒》的論述中,引證毛澤東曾用《黔之驢》寓言來分析日本侵略軍日暮途窮的結局,稱為「『古為今用』之輝煌典範」。這些都是比較顯著的引用。《指要》有時還借題發揮,如在《柳子厚生於今日將如何》中由防微杜漸而批判前蘇聯「向修正主義奔去」(1279頁)、《禮樂為虛器論》中批判「蘇聯領導人名尼基塔者」(1313頁)、《息壤》中由「息壤」一詞而抨擊蘇美戴維營會談,斥責赫魯曉夫(1961頁)等處,雖可以看出著者的政治熱情和文人氣質,但總不免對古為今用有簡單生硬的理解。正因如此,《指要》一書問世之後,也引起了一些困惑和疑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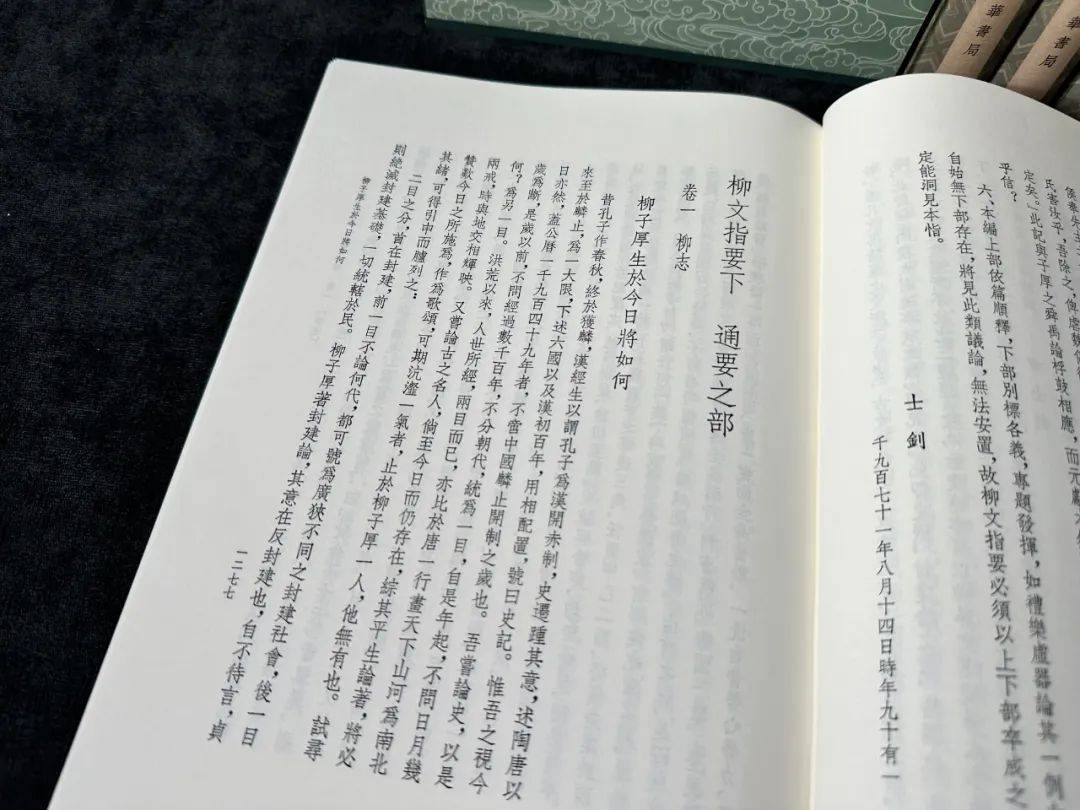
我們覺得,《指要》一書是一部研究古典文學的學術著作,其中雖有一些偏頗和過激的言論,但基本上還是柳文研究的一家之言。聯繫現實政治和借今釋古的地方畢竟只是少量的,大概只佔全書百分之三四。從整體上看,談的都是有關柳宗元和柳文的學術問題。關於二王八司馬的評價,關於韓柳優劣的議論,歷來都有不同的意見,《指要》總結前人乃至今人的成果,提出自己的看法,這完全是百家爭鳴範圍的事。章士釗先生以六七十年的積累,在晚年寫出這樣一部巨著,對柳文的研究很有參考價值,具有相當大的學術價值和文化積累價值。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為一部體現文化政策、雙百方針的典型出版物,更有其獨特的歷史意義。
(2024)
========
- [12/14]美國「文革」成果:新一代大學生不會讀、不會寫、不會思考
- [12/15]新三代做舊夢?八零后「老淚縱橫」,你什麼感覺?
- [12/17]一百年前的毛澤東:願做個無根的流浪者
- [12/17]魯迅的性格
- [12/26]平安夜訪轉獄后的美國「一六「政治犯和家屬
- [12/27] 毛澤東對柳宗元的鐘愛
- [12/27]哺乳可黑紋國家實驗室 2024 年十大發現
- [12/28]從不休息不過年每天半夜后休息的99歲小鎮醫生-謝春梅
- [12/28]安慰詩: 就讓他們去吧
- [12/31]便秘頌
- [12/31]黃蜂的復仇
- [12/31]明星校長鄭強不裝了 脫口秀自稱丫鬟
- [01/03]2024 猶太詩人之 孤月頌
- 查看:[change?的.最新博文]
- 查看:[大家的.最新博文]
- 查看:[大家的.文史雜談]
評論 (0 個評論)
- goofegg:作協和詩刊的盛宴及資本的狂歡
- bobzhou:向毛澤東的生日獻禮
- 顧曉軍53: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涉2大案 北檢求刑合計28年半
- 文廟:網路和人工智慧喚醒了我的坐家文學夢
- bobzhou:二百年這些聖誕老人給中國人帶來文明
- 顧曉軍53:世界因為有這三個狠人在 未來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 Brigade:血腥瑪麗
- bobzhou:上海市民回顧1988年「平安夜」初體驗
- 蘇誠忠:被人拽起
- 謝盛友:先後嫁給父子的楊貴妃
- bobzhou:再看赫魯曉夫是怎樣下台的
- bobzhou:永遠不能忘記這個冬至日
- 蘇誠忠:同樣集權,不一樣的後果
- 顧曉軍53:我與李鐵的恩怨情仇
- 顧曉軍53:在川普身上,我看到了另一種小人得志
- change?:在莫衷一是的時代浮沉之 楊度的眼光與才幹
- 蘇誠忠:資本主義是民主的基石
- 顧曉軍53:我為瓊瑤說幾句
- bobzhou:曾經讓美國『偉大』的胡佛總統
- bobzhou:陳良宇才是真正的上海足球的教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