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答聶文蔚》 [2017/04]
- 奧巴馬致女友:我每天都和男人做愛 [2023/11]
- 愛國者的喜訊,干吃福利的綠卡族回國希望大增 [2017/01]
- 周五落軌的真的是個華女 [2017/03]
- 現場! 全副武裝的警察突入燕郊 [2017/12]
- 法拉盛的「雞街」剛剛又鬧出人命 [2017/11]
- 大部分人品太差了--- 中國公園裡的「黃昏戀」 [2019/12]
- 亞裔男孩再讓美國瘋狂 [2018/09]
- 年三十工作/小媳婦好嗎 /土撥鼠真屌/美華素質高? [2019/02]
- 看這些入籍美加的中國人在這裡的醜態百出下場可期 [2019/11]
- 黑暗時代的明燈 [2017/01]
- 文革宣傳畫名作選之 「群醜圖」 都畫了誰? [2024/01]
- 當今的美國是不是還從根本上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 [2017/10]
- 香港的抗爭再次告訴世人 [2019/06]
- 中國女歡呼日本地震 歐洲老公驚呆上網反思 [2024/01]
- 加入外國籍,你還是不是中國人?談多數華人的愚昧和少數華人的覺醒 [2018/02]
- 周末逛法拉盛,還是坐地鐵? [2017/10]
- 春蠶到死絲方斷, 丹心未酬血已干 [2017/03]

熱門:230 Fifth Rooftop Bar是曼哈頓最熱鬧的露天酒吧之一,吸引了形形色色的顧客。周一晚,費吉·梅耶(Faigy Mayer)當著其他顧客的面從酒吧頂樓跳下。
獨家報道:從紐約屋頂酒吧跳樓自殺的女子生前曾給朋友寫過一封令人心碎的信,講述了她在嚴格的哈西德猶太教家庭中遭受的痛苦,以及她放棄信仰后如何掙扎求生。
>> More Videos
230 Fifth Rooftop Bar
30歲的費吉·梅耶(Faigy Mayer)周一從紐約一家時尚的屋頂酒吧20層樓高的地方跳下,當時酒吧里還有其他顧客。
她在紐約布魯克林長大,接受哈西德猶太教的熏陶,但在24歲時離開了猶太教,並一直難以接受與家人分離的現實。
一位朋友透露,她在去世前一周寫了一封信,解釋了她童年時期缺乏朋友的痛苦。
梅耶描述了她在哈西德教世界之外如何難以進行「分析性思考」,並憤怒地談到拉比們的「勝利」。
朋友們說,她當時正飽受精神健康問題的困擾,同時還面臨著被驅逐和找工作的困境。
昨天,她被哈西德教社區安葬,她的父親在葬禮上用英語和意第緒語發表了講話。
一位科技創業公司創始人從紐約市一家屋頂酒吧跳樓自殺。在她去世前一周,她寫了一封令人心碎的信,哀悼自己孤獨的哈西德猶太教童年和與世隔絕的成年生活。
30歲的費吉·梅耶(Faigy Mayer)在信中飽含真情地描述了她對在紐約布魯克林長大的那個嚴苛而封閉的世界的感受。
她指責哈西德教派限制了信徒的思維,並寫道自己至今仍在努力克服分析性思維的障礙。
梅耶將這封信發給了她的好友楊波·杜(Yangbo Du),杜將信件內容透露給了《每日郵報》在線版,稱這封信展現了她所遭受的痛苦。他還透露,費吉·梅耶在7月12日發送那條信息時,正面臨被房東驅逐的困境,並且正在尋找工作。
「我的族人」:費吉·梅耶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一張圖片的配文。五年前,她離開了自己從小長大的哈西德派社區。

「我的族人」:費吉·梅耶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一張圖片的配文。五年前,她離開了從小長大的哈西德派猶太社區。

世俗生活:費吉·梅耶選擇離開她從小長大的嚴格的貝爾茲哈西德派猶太社區,過另一種生活。但她在去世前寫的一封信揭示了她離開前後所遭受的痛苦。

悲劇:費吉·梅耶24歲時離開了她的哈西德派猶太社區。這個決定導致她與父母關係疏遠。

在信中(全文如下),她寫道:「我記得三年級的時候,我和媽媽列了一張名單,上面都是我所在的哈西德猶太女子學校 (girls-only hasidic Jewish girls' school)里的女孩。這所學校屬於貝爾茲哈西德教派(of the Hasidic sect of Belz)。
「目的是為了幫我找個朋友。我們一起看了名單,看看有沒有我想交朋友的人。我不記得看完名單之後發生了什麼。
「但我確實記得,顯然什麼也沒做成,直到24歲我離開哈西德猶太教,我才交到朋友。」
梅耶認為,她與哈西德社群的疏離感源於「她外公外婆皈依了哈西德猶太教」。
她寫道:「我祖母18歲時就從布魯克林學院獲得了大部分大學學位,她才智過人,我繼承了她的才華,並強烈認同我的美國血統。」
「我沒法和同齡人聊些什麼。我無法和他們分享我對閱讀奧運會書籍的熱愛。」
她形容自己的學校是一個「嚴酷的環境」,在那裡她「故意掛科,放棄了意第緒語」。
「如果人們可以自由思考,他們就不會信教了」:費吉·梅耶寫給朋友的悲傷遺書
梅耶認為,她與哈西德派社群的疏離感源於她「外祖父母皈依了哈西德猶太教」。
她寫道:「我祖母18歲時就從布魯克林學院獲得了大部分大學學位,她才華橫溢,我繼承了她的才華,並強烈認同我的美國根源。」
「我和同齡人沒什麼共同話題。我無法與他們分享我對閱讀奧運會書籍的熱愛。」
她形容自己的學校是一個「嚴苛的環境」,在那裡她「故意掛科,放棄了意第緒語課程」。
「如果人們可以自由思考,他們就不會信教了」:費吉·梅耶寫給朋友的悲傷遺書
我記得三年級的時候,我和媽媽列了一張名單,上面都是我們學校里所有女生的名字。我們學校是哈西德派猶太教的女子學校。
我們列名單的目的是為了幫我找個朋友。我們一起看了看名單,看看有沒有我想結交的朋友。我不記得列完名單之後發生了什麼。
但是,我清楚地記得,這件事最終一無所獲。直到24歲我離開哈西德派猶太教之前,我都沒有朋友。
我以為十年級的時候,一個叫雪佛蘭的女孩是我的朋友。但是當她不得不告訴她妹妹我去了她家時,她說:「我的同學來了。」我記得她不稱我為朋友時,我感到很受傷。
直到最近慶祝了我離開哈西德猶太教五周年,我才意識到我的問題可能出在哪裡。
這大概是因為我外公外婆是哈西德猶太教的皈依者,我外婆18歲就拿到了布魯克林學院的大部分學位,她才華橫溢,而我繼承了她的特質,並強烈認同我的美國根源。
我和同齡人之間沒什麼共同話題。我無法和他們分享我對閱讀奧運書籍的熱愛。
直到24歲離開哈西德猶太教,我才交到朋友。我以為十年級時一個叫雪佛蘭的女孩是我的朋友,但當她不得不告訴她妹妹我去了她家時,她說:「我的同學來了。」 我記得她不稱我為朋友時,我感到很受傷。
我七年級時很喜歡我的老師比內特太太。她很酷。貝爾茲學校的右翼思想非常嚴重,規定所有已婚教師如果戴的是假髮而不是絲巾,就必須在假髮上再戴一頂帽子。
比內特太太因為帽子戴得稍微花哨一點就被訓斥了。學校不鼓勵追求時尚。這就是我當時所處的嚴苛環境。
直到23歲,一位世俗的親戚告訴我,我才知道離開哈西德教派也是一個選擇。我當時也不知道,我永遠不可能嫁給一個哈西德派教徒。
16歲那年,我那沒受過什麼教育的母親親自診斷我患有雙相情感障礙。18歲時,考慮到當時的家庭情況,我被允許上大學,後來又讀了研究生。
但我記得,在我18歲左右的時候,我曾想過,如果我生的是男孩會怎麼樣?在貝爾茲學校,從學前班到高中畢業,每天的課程都被分成兩半。
一天分為兩部分:前半部分是「意第緒語」,後半部分是「英語」。我故意讓意第緒語掛科,因為我知道不會有什麼後果,英語和意第緒語的文憑是分開頒發的。
2004年8月,18歲的我憑藉畢業證書被圖羅學院錄取,但我沒有成績單,因為哈西德派學校拒絕提供成績單。
但哈西德派男孩就沒有女孩那麼幸運了。他們連除法或分數之類的簡單數學都不會。這是因為他們的一天沒有分成兩部分,他們整天都只學習「意第緒語」。
我記得當時我在想,如果我有個兒子,讓他整天遭受學習意第緒語的折磨,我會怎麼辦?
我記得我的老師吉普斯太太教我們猶太教飲食律法(kashrut)的時候,她特別在意我不小心把奶製品器具放進了肉鍋里。當時我甚至不知道「胡扯」這個詞,心裡想的就是這個。結果,掛科了,而且掛了很多其他科目,這反而是我做過的最明智的事。
我當時還不知道自己是不可知論者,所以拒絕學習那些顯然已經不適用於2001年的規矩。六年級的時候,我就開始學《安息日三十六誡》(Lammed Tes Meluchos)了,情況也是如此。
《安息日三十六誡》指的是安息日要遵守的三十六條誡命。我記得其中一條誡命禁止在安息日打結,而我的老師教了我們所有打結和解結的漏洞。
我因為裝飾我的《安息日三十六誡》書,把它弄得太花哨而被老師批評,但我卻從未真正學習過我精心書寫的那些希伯來語單詞。
我之所以討論以上內容,是為了解釋那些在美國長大的聰明孩子會面臨什麼。
然而,我覺得哈西德猶太教根本就不應該存在。我的三個侄子在非常嚴格的哈西德猶太教環境中長大。他們被迫這樣生活,這對他們來說太不公平了。他們最大的樂趣就是用蠟筆塗色。
即使我被允許參與他們的生活,他們也不被允許玩我的iPhone遊戲。
美國孩子每天都能享受到的基本樂趣,我的侄子們卻無法體驗。相反,他們要在切德爾(Cheder,一所男校)里長時間學習,被迫坐在一個地方學習猶太教律法和歷史,完全沒有時間進行體育運動。

費吉·梅耶:一位朋友公開了她去世前幾天寫的一封信

逝世:30歲的費吉·梅耶爾(Faigy Mayer)創辦了自己的初創公司,該公司正在開發一款應用程序,幫助那些脫離哈西德派猶太教信仰、努力適應紐約市喧囂生活的猶太人。

逝世:30歲的費吉·梅耶爾(Faigy Mayer)創辦了自己的初創公司,該公司正在開發一款應用程序,幫助那些脫離哈西德派猶太教信仰、努力適應紐約市喧囂生活的猶太人。
今天我在電視上看了羅傑·費德勒在溫布爾登網球公開賽上的比賽,和我一起看電視的人解釋說,通常情況下,冠軍需要贏3分。我原本以為我的侄子們永遠也看不到網球比賽。
但昨晚我和兩位朋友楊博·杜(Yangbo Du)和傑森(Jason)的談話卻讓我改變了看法。
傑森和楊博在討論Facebook如何巧妙地利用市場營銷手段,創建了一個名為internet.org的501c3非營利組織,為使用facebook.com的用戶提供免費網路連接,從而賺取廣告收入。
然後,如果用戶使用facebook.com以外的域名,Facebook還會收取費用,從中牟利。我不同意傑森的觀點,他認為Facebook不應該這樣做。
我明白無神論的哈西德派猶太人是如何假裝相信的,而Facebook是他們與志同道合的猶太人交流的唯一渠道(除非Facebook發現他們的賬戶是假的,並自動刪除)。
但是,拉比們不允許使用電腦或智能手機,所以internet.org對我的族人沒有任何幫助。
接下來我們談話的內容,我想會讓大家大開眼界。
我的族人過著極其簡樸的生活:包辦婚姻、嚴格的性別隔離、妻子剃光頭、夫妻在完全黑暗的環境下(床單上有個洞)做愛,妻子卻只穿胸罩,但一生中通常要生育13個孩子,只能靠現金工作,這樣才能領取政府的食品券、第八條款住房補助和醫療補助,而且由於醫療保險最差,他們平均只能看最差的醫生。
傑森認為這種情況或許會在20年內結束。
傑森的房東是哈西德派教徒,所以他舉了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他的邏輯:房東三周都沒回復他關於空調壞了的郵件。結果,他的電費賬單飆升,他拒絕支付一個月的房租。
傑森說,房東解釋說她沒有網路,所以無法及時回復他的郵件。
然而,既然她損失了一個月的房租,她會想辦法每天查看郵件嗎?很可能會。
我覺得哈西德猶太教根本就不應該存在。我的三個侄子在非常嚴格的哈西德猶太教環境中長大。他們被迫這樣生活,這對他們來說太不公平了。他們最大的樂趣就是用蠟筆塗色。
現在,拉比們佔了上風。邪教的特徵之一就是擁有魅力領袖。這些魅力四射的拉比們正在抵制互聯網。但是,沒有互聯網,你能活下去嗎?
大學期間,我曾在我姑姑家做兼職,大概五年。她和我叔叔在家經營一家滅蟲公司。家裡沒有網路,他們面臨著巨大的困難。
自從我不再為他們撰寫化學品使用報告后,他們就讓他們的顧問來做。他們的顧問必須親自到博羅公園(Boro Park)來,把數據放到U盤裡,然後她才能進行處理。這是現在的情況。
當我需要更新紐約州身份證時,我是在網上辦理的。如果20年後,你必須上網才能為孩子辦理出生證明,那該怎麼辦?我的出生證明是紙質的。這合理嗎?
一位哈西德派母親有13個孩子,她需要這些出生證明才能在孩子出生后立即申請食品券。
她會上網申請食品券嗎?我相信她會。一旦她上網,她可能會在首頁看到一些故事,這些故事可能會讓她反思自己艱辛的生活——她接受這種生活,但卻不加思考。
如果人們可以思考,他們就不會信教了。
在面對基本的生活抉擇時進行分析性思考,對我來說是全新的體驗,即使離開教派五年後,我仍然在努力適應。
梅耶爾說,16歲時,「我那沒受過什麼教育的母親親自診斷我患有雙相情感障礙」。
梅耶爾寫道,直到23歲,一位世俗的親戚告訴她她可以放棄宗教信仰后,她才開始考慮放棄宗教。
「我當時並不知道我永遠不可能嫁給一個哈西德派教徒,」她寫道。
但這篇長文也流露出她與三個侄子分離的痛苦。
「我的三個侄子在一個非常嚴格的哈西德派猶太教環境中長大……即使我被允許參與他們的生活,他們也不能玩我的iPhone遊戲。」
梅耶爾還更廣泛地探討了為封閉的哈西德派世界提供互聯網接入的好處。但她總結道:「如果人們被允許思考,他們就不會信教了。」
「在面對基本生活抉擇時進行分析性思考對我來說是全新的體驗,即使離開五年後,我仍然在努力克服這個問題。」
企業家杜先生最後一次見到梅耶是在7月15日曼哈頓切爾西區的一個科技研討會上。
他告訴《每日郵報》在線版,梅耶當時看起來狀態不錯,但他形容她「正在努力重整生活,而且經常情緒低落」。
杜先生告訴《每日郵報》在線版,自從他們相識以來,梅耶已經多次住院。他說,她最近一次住院是在四月份,再之前是在三月份。

熱門:230 Fifth Rooftop Bar是曼哈頓最熱鬧的露天酒吧之一,吸引了形形色色的顧客。周一晚,費吉·梅耶(Faigy Mayer)當著其他顧客的面從酒吧頂樓跳下。
費吉·梅耶
逝世:30歲的費吉·梅耶創立了自己的初創公司,開發一款應用程序,幫助那些脫離哈西德派猶太教信仰、難以適應紐約都市喧囂生活的人們。
另一位朋友門德爾·凱勒(Mendel Keller)通過一個哈西德派猶太教脫離者互助小組認識了梅耶,他告訴《每日郵報》在線版,梅耶至少兩次住院。
另一位朋友,26歲的莉貝爾·波拉基(Libelle Polaki)告訴《每日郵報》在線版,梅耶一直在與抑鬱症作鬥爭,她自殺的原因是她痛苦地脫離了父母的宗教信仰,因為她「不想成為20個孩子的母親」。
杜和梅耶爾在二月份梅耶爾參加的第一次黑客馬拉松上相識。當時她開發了一款幫助無家可歸者的應用程序。
黑客馬拉松是一種周末舉辦的編程競賽,旨在幫助程序員磨練技能。它與試圖入侵安全系統造成破壞或竊取數據無關。
杜說,梅耶爾在他們初次見面時告訴他,她與哈西德猶太社區失去了聯繫。他幫助她結識了紐約科技圈的人,在那裡她找到了自己對編程的熱情。
杜說,周六晚上,這位嶄露頭角的科技創業者聯繫了他,請求他幫忙找工作。
「她想找全職、兼職甚至按小時計酬的工作,並告訴我她將在60天內被房東趕出公寓,」他說。
杜說,他認為梅耶爾在布魯克林威廉斯堡與室友合租了一套公寓,但「合租安排並不順利」。
悲痛欲絕:周一從曼哈頓一家酒吧墜亡的梅耶爾的親朋好友聚集在一起,為她舉行葬禮。

悲痛欲絕:周一從曼哈頓一家酒吧墜亡的梅耶爾的親朋好友聚集在一起,為她舉行葬禮。

社區:布魯克林哈西德猶太社區的成員們參加了費吉·梅耶爾的葬禮。
幾個月來,這位30歲的女子似乎一直在試圖擺脫目前的居住環境。
6月10日,梅耶爾給杜發簡訊說:「你好,楊波,你介意把你的房子分割成幾間讓我住嗎?」
杜的公寓已經分割好了,於是他推薦了一位正在尋找合租房的朋友。五天後,梅耶爾再次給他發簡訊,想找個地方住。
「你好,楊波,你的鄰居有空房可以轉租嗎?」梅耶爾寫道。
6月底,梅耶爾再次聯繫杜,說她在布魯克林皇冠高地租的房子沒租成,問他是否知道哪裡有房子出租。杜給她發了一些公寓信息,並提出可以暫時讓她住幾天。
她回復說:「但是要住多久呢?……我現在住的地方法律上是可以住的……謝謝你的好意。」
但上周參加完科技活動后,梅耶爾上周末聯繫了杜,請求他幫忙找工作,並告訴他自己收到了正式的驅逐通知。
周一晚上,梅耶爾從曼哈頓第五大道230號酒吧的樓頂跳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據莉貝爾·波拉基(Libelle Polaki)說,她最後一次見到梅耶爾是在六月份,當時梅耶爾情緒低落。波拉基表示,雖然其他因素也可能導致梅耶爾自殺,「但她的過去和家庭狀況可能加劇了這種情況」。
梅耶爾的母親查瓦·梅耶爾(Chava Mayer)告訴《每日郵報》在線版:「我不想說任何話。我還能說什麼呢?說她是個好人嗎?不,我們不想評論。」這令人悲傷地表明了她與信仰決裂所帶來的影響。
梅耶爾的父親以色列·梅耶爾(Israel Mayer)也拒絕發表評論。在布魯克林的Shomrei Hadas教堂,親朋好友聚集在一起,為她舉行了一場令人動容的葬禮。
然而,昨天他在葬禮上致辭時,卻用英語開場,這被視為他試圖與哈西德教派以外的人交流的舉動。
波拉基告訴《每日郵報》在線版,費吉在23或24歲時脫離了哈西德教派。
「宗教生活方式不適合她。它永遠無法讓她擁有自己的生活和個性。」
「我們上的是一所管教極其嚴格的高中。那段日子非常難熬。」
「她不想成為20個孩子的母親。她不想被束縛,她渴望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才能,而且她非常聰明。」
「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年裡,她有一些朋友,他們支持她,接納她本來的樣子。」
但她或許難以適應與如此緊密的社群決裂。
波拉基說:「她來自一個大家庭,她深愛著她的侄子侄女們,她很想念他們。」
波拉基小姐說,她並不知道她的朋友在感情方面有什麼問題,雖然她可能正在約會,但在她去世時並沒有男朋友。
波拉基說,她最後一次見到朋友是在6月19日的瑞典節上,她說,朋友離開的決定給她帶來了深深的焦慮。
喬納森·科貝特是費伊的朋友,兩人已經認識兩年了。科貝特是一名31歲的軟體開發人員,他告訴《每日郵報》在線版,他認為離開費伊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封閉社區對她的情感和心理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
他說:「很明顯,她失去了從小一起長大的人們的愛,生活很艱難。」
儀式:7月,在布魯克林的Shomrei Hadas教堂,人們為Faigy Mayer的遺體舉行祈禱儀式。

儀式:在布魯克林的Shomrei Hadas教堂,人們為Faigy Mayer的遺體舉行祈禱儀式。

哀悼:周一去世的Faigy Mayer的親友聚集在布魯克林的Shomrei Hadas教堂,悼念她的離世。

哀悼:周一去世的Faigy Mayer的親友聚集在布魯克林的Shomrei Hadas教堂,悼念她的離世。

最終安息地:周二,Faigy Mayer的遺體從Shomrei Hadas教堂被運往墓地。
在紀錄片中,她講述了自己從小就對意第緒語和希伯來語不感興趣。
「我當時想儘快離開,」梅耶爾說,「這在情感上極具挑戰性。」
該節目講述了她與「足跡」(Footsteps)組織合作的經歷,該組織致力於幫助那些離開極端宗教猶太社區的人。
「我的父母直截了當地告訴我,你必須離開這裡,因為你不再信教了,」梅耶爾說道。她還補充說,她的父母最終還是接納了她。
梅耶爾曾是一名iOS開發人員,並創立了自己的初創公司Appton。她當時正在開發一款應用程序,幫助那些離開哈西德派猶太教家庭的人在艱難地離開家庭后更好地融入紐約的生活。
據目擊者稱,周一晚上7點30分左右,梅耶爾沖向曼哈頓熨斗區230 Fifth Rooftop Bar屋頂邊緣的一排灌木叢。
她翻過圍牆,落在了20層樓下的西27街人行道上。
「我當時正過馬路,看到她摔倒了,」目擊者戴爾·馬丁告訴《紐約郵報》。「看得出來她是一位女士。她穿著鞋子和裙子。」
心碎:費吉·梅耶(左)和她的朋友莉貝爾·波拉基在6月19日共同參加的瑞典夏季集市上合影

心碎:費吉·梅耶(左)和她的朋友莉貝爾·波拉基在6月19日共同參加的瑞典夏季集市上合影

獨自闖蕩:費吉參與了國家地理頻道播出的一部紀錄片,該片探討了離開極其保守的宗教所帶來的影響
傾訴:互助小組「足跡」(Footsteps)幫助梅耶(右)接受了她離開哈西德派背景的決定

傾訴:互助小組「足跡」(Footsteps)幫助梅耶(右)接受了她離開哈西德派背景的決定
「很難說……」 「基本上是被排斥對她造成的影響。」
他說:「費吉有心理醫生可以諮詢,她服用藥物,也有朋友可以傾訴,但她最終決定這樣的生活不適合她。」
「在布魯克林這個小小的圈子裡生活了25年後,她經濟拮据,不得不另謀生路,但她最終對編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然而,她面臨著重重阻礙。」
她的困境促使她參與了2012年國家地理頻道的紀錄片《哈西德教內幕》(Inside Hasidism)。這部紀錄片探討了這個神秘宗教社群所承受的獨特壓力,僅在紐約市就有約12.5萬名信徒。
梅耶在紀錄片中解釋說,她拒絕了哈西德教,因此被父母趕出了家門,不過她說後來又和他們團聚了。
在美國,如需保密支持,請撥打全國預防自殺熱線 1-800-273-8255。
在英國,如需保密支持,請撥打撒瑪利亞會熱線 08457 90 90 90,訪問當地撒瑪利亞會分支機構或訪問 www.samaritans.org。
路易絲·博伊爾報道每日郵報網站
發布時間:美國東部時間2015年7月22日
哈西德教: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
HASIDISM: A SEPARATE LIFE哈西德教是正統猶太教的一個分支,起源於18世紀中葉的東歐,曾被數百萬猶太人接受,但在納粹大屠殺中幾乎消失殆盡。
二戰後,猶太移民將哈西德教帶到美國,並傳播到以色列、西歐、澳大利亞和加拿大。
哈西德教社群在相對封閉的社區中遵循嚴格的宗教傳統,使用意第緒語——東歐猶太人的語言。孩子們在家說意第緒語,在學校也用意第緒語學習,社群還支持報紙和圖書出版。
美國最大的哈西德教社群位於布魯克林,估計有16.5萬哈西德教徒居住在那裡,主要集中在博羅公園、威廉斯堡和皇冠高地。
在這些社區內,還有一些被稱為「庭院」(courts)的小型社群,有些庭院甚至只有幾個家庭。
每個教派都向拉比(rebbe)尋求宗教方面的指導,這些宗教事務涵蓋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每個教派都以其祖先的故鄉命名:貝爾茲教派來自今天的烏克蘭,盧巴維奇教派來自俄羅斯,博博夫教派來自今天的波蘭。
每個教派,也稱為一個宗派,對哈西德派的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都有不同的詮釋,但許多傳統是重疊的。除了宗教儀式,哈西德派社群還擁有悠久的口頭講故事傳統,以及獨特的歌曲和舞蹈。
哈西德派男子留著長長的鬍鬚,鬢角捲曲,通常身著黑色長袍,頭戴帽子。



紐約布魯克林哈西德教猶太人集聚區



哈西德派女孩從小就被要求穿著寬鬆的衣服,從腳踝到手腕遮蓋身體,並穿著高領服裝。
一些宗派要求女性在結婚後剃光頭並佩戴假髮,而另一些宗派則要求她們用頭巾和帽子遮蓋頭髮。
哈西德派強調女性要保持安靜順從,並遵守「zeni'ut」(謙遜)的戒律。女性每月月經結束后必須進行名為「mikveh」的浸禮儀式。
男女通常通過媒人相識,但婚姻需要男女雙方的同意。他們被期望與本社區成員通婚。
在社交場合,男女之間不會混雜;在度假勝地,男女不能共用游泳池;男女不能接受同校教育。
婚姻通常在十幾歲末或二十歲出頭舉行。根據宗教教義,哈西德派猶太教徒擁有龐大的家庭,因為孩子是上帝的恩賜,節育是被禁止的。
據aish.com網站報道,哈西德派夫婦平均生育八個孩子。
哈西德派擁有獨立的學校系統。從學前班開始,男孩和女孩就分開上課,男孩隨著年齡的增長學習時間也會增加。
哈西德教派在給予女孩的教育水平和職業機會方面存在差異。
傳統上,女孩的教育包括更多的英語和歷史課程以及宗教課程。
男孩則學習《塔木德》,這是猶太教的核心經典。
《塔木德》(希伯來文:תלמוד,Talmud,為教導或學習之意)除猶太教卡拉派外,在主流猶太教中地位僅次於《塔納赫》的宗教文獻。源於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5世紀間,記錄了猶太教的律法、條例和傳統。其內容分三部分,分別是密西拿──口傳律法、革馬拉──口傳律法註釋、米德拉什──聖經註釋。
由於《革馬拉》分為以色列與巴比倫兩個版本,因此《塔木德》也分為《耶路撒冷塔木德》(或稱《巴勒斯坦塔木德》)及《巴比倫塔木德》。
結構與功用
猶太教的拉比一向認為,猶太教的承傳除了律法書以外,還有一本與之一同相傳的口頭傳統習慣。塔木德就是這一本記載猶太人傳統口耳相傳的生活習慣的書。這本書可以分為二部分:密西拿和革馬拉。
塔木德內容大約有二十卷到五十卷之多,約一萬兩千多頁,兩百五十多萬字。目前為止,已經被翻譯成十二種文字。塔木德的內容主要分為三大部分,分別是《密西拿》、《革馬拉》、《米德拉什》,自公元二世紀中期以來,由一代一代的猶太人分別以口頭或文書紀錄記錄下來的行為及道德規範等,被全數收入猶太法律總集《密西拿》中,後來經過猶太學者對其中問題的討論以及經過時代的演變,又有猶太學者編著成了《革馬拉》,其後,又進一步補充而成了《米德拉什》。
塔木德的內容講述的包涵了人生各個階段的行為規範,以及人們對人生價值觀的養成,是猶太人對自己民族和國家的歷史、文化以及智慧的探索而淬鍊出的結晶。
參見
猶太教主題
icon 書籍主題
《塔納赫》──猶太教希伯來聖經正典
《塔木德》
《密西拿》──口傳律法
《革馬拉》──口傳律法註釋
《米德拉什》──聖經註釋
- 《塔木德》網上全文:
- Mishna Archive.today的存檔,存檔日期2012-12-05
- Tosefta Archive-It的存檔,存檔日期2013-10-11
- Talmud Yerushalmi Archive-It的存檔,存檔日期2013-10-11
- Talmud Bavli Archive-It的存檔,存檔日期2013-10-11
- 1903年Rodkinson的英譯本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只有Moed及Nashim)
- 被巴比倫擄時的塔木德(圖片)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Pertaining to the "Daf Yomi" program:(關於「每日一頁經文」計劃:)
- General:
- 巴比倫塔慕德(塔木德)中文版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猶太法典Talmu一d-塔木德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A Page from the Babylonian Talmud"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image map from Prof. Eliezer Segal
- A survey of rabbinic literatur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on the Ohr Somayach website
- point by point summary and discussion by daf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Jewish Law Research Guide, University of Miami Law Library
- Refutation of anti-Semitic allegations concerning the Talmud(駁斥有關《塔木德》的反猶太主義指控:):
雖然哈西德教男子通常在婚後幾年內繼續學習《托拉》,但他們上大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妥拉(希伯來語:תורה,英語:Torah),中文別稱托拉,廣義上指上帝啟示給以色列人的真義與人類教導指引,狹義上特指猶太教核心經典《摩西五經》的統稱,猶太教稱為摩西律法(希伯來語:תורת־משה,Torat Moshe)(猶太人不稱舊約),包含《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五卷,記載了以色列民族的起源、出埃及曆程及律法體系。其內容涵蓋宗教戒律、民事法規與祭祀條例,包括摩西十誡等613條細則,被視為上帝與以色列人立約的憑證 。
該經典用希伯來文寫成,主體內容形成於公元前6世紀巴比倫囚虜時期,通過彙編古代文獻強化民族信仰認同 。傳統認為摩西接受上帝啟示創作五經,但《申命記》末章明確記載其逝世經過,中世紀學者指出部分章節存在第三人稱敘述與歷史回溯,質疑單一作者論。16世紀後學界普遍認為五經由多文本彙編而成,具體成書過程尚無定論 。
猶太民族又被稱為「書的民族」,這裡所謂的「書」,實際就是指希伯萊文經卷,其中最重要的「經書」莫過於《托拉》。千百年來,猶太人一直視《托拉》為「經典中的經典」。
托拉Torah 廣義泛指上帝啟示給以色列人的真義, 亦即上帝啟示給人類的教導或指引。狹義常指《舊約》的首五卷,又稱律法書或《摩西五經》,即:《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末記》、《民數記》與《申命記》。但猶太人不用「舊約」一詞,因為《舊約》是相對《新約》而言的,而後者為基督教文獻。誦讀律法是猶太教禮拜儀式的一項重要內容。托拉也指全部希伯萊聖經。有時也包括口傳立法和成文立法。有人認為眾拉比對口傳律法與成文律法的評註與解釋無非是口頭聖傳的沿伸,因此「托拉」一詞的含義進一步擴大而包含全部猶太律法、習俗及禮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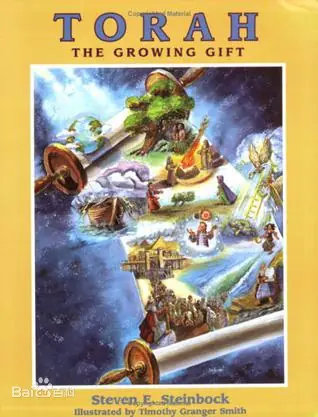
作為一部古書,《托拉》是猶太人民心靈的反映,智慧的結晶。
正統的猶太教一向認為《托拉》是「上帝的立言」,是上帝授於摩西的聖書。儘管有些人也承認這本神聖的經書因代代傳抄,難免出現這樣那樣的錯誤,但他們堅信《托拉》出自神之手,而非人之手。原教旨信徒堅持上帝之言句句是真理,不可增一字,不可減一字,如果現代科學知識與之有矛盾,那麼不是科學出錯,便是人們的理解有誤。
有一種觀點認為,上帝雖非如原教旨主義者所說的那樣是《托拉》的作者,但這部書畢竟是人類對上帝的理解和體驗。千百年來,這種理解和體驗並非一成不變,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變遷。最初的經文是口耳相傳,經過許多代后才寫定成文,最終的文本反映了猶太人先祖對上帝和人類的看法,而且可以看出其信仰發展變化的痕迹,由此可見,《托拉》並非出自上帝之手,而是出自先民之手,它帶有猶太先祖的印記,記錄了以色列先民對上帝獨特的感受。《托拉》是人們企望記載人與上帝相遇時那非凡的一刻。他們由此推論,儘管《托拉》的作者是人而不是神,人們卻可以憑此聽到上帝的聲音。(註:W.C.伯拉特:《托拉新注》,紐約1967年第20頁。)
二千五百多年來,《托拉》一直是猶太人生活的精神基石,對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興起也有著深刻的影響,它曾經並仍然在世界上起著非同小可的作用。西方人之所以為當今之西方人,部分原因在於《托拉》所言和所欲言,在於人們信仰《托拉》曾所言和所欲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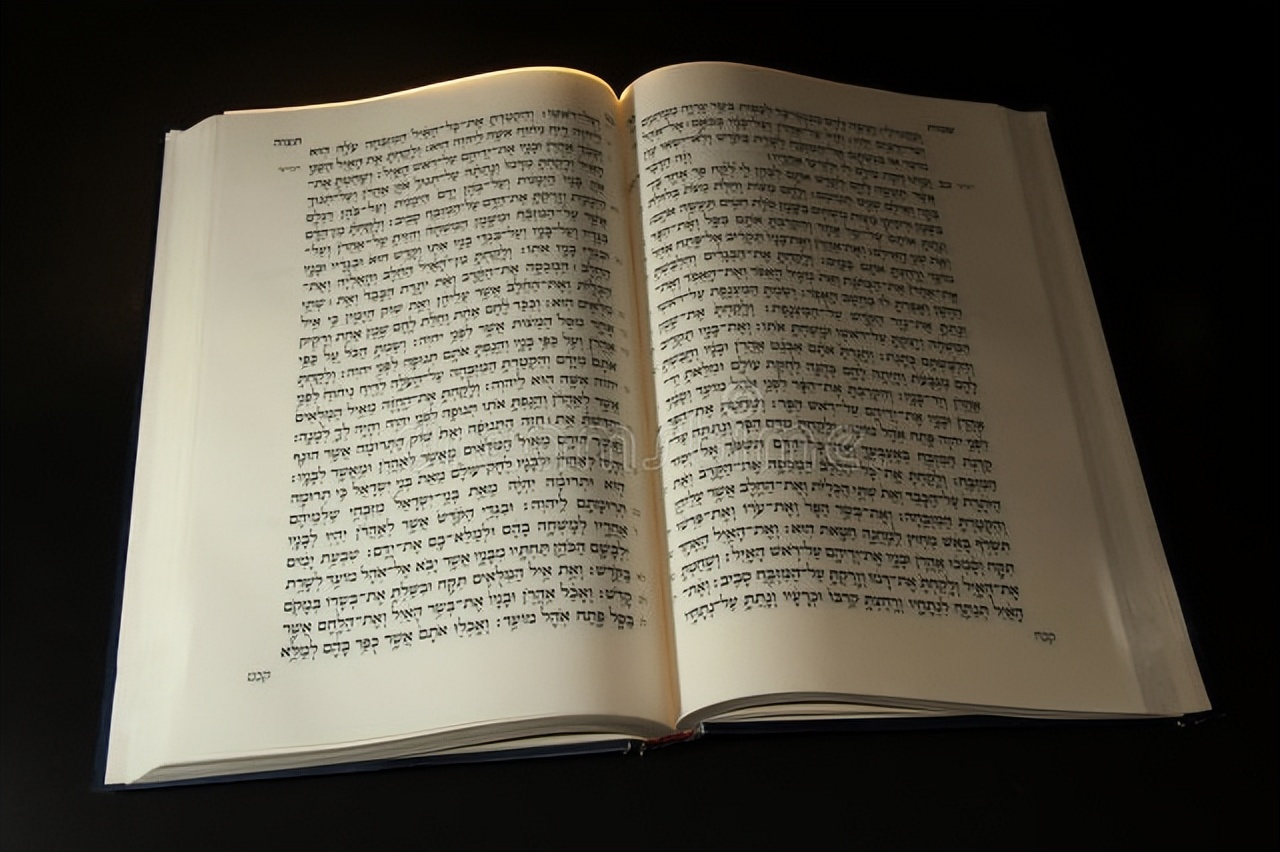
==========
Z世代偶像? 再看一位「特立獨行」比金斯伯格男人氣N倍的自由派猶太女大嘴---弗蘭·勒博維茨

弗蘭·勒博維茨:「跨性別者的權利除了當事人之外,對任何人都沒有影響。所以你為什麼要關心?」
這位紐約作家兼新晉Z世代偶像與佐伊·比蒂暢談特朗普主義、跨性別者的權利,以及為何在互聯網時代無法進行冷靜的對話。
星期日,美國東部時間凌晨1點
弗蘭·勒博維茨:「我會評判每件事……這就是我觀察世界的方式」(Netflix)
弗蘭·勒博維茨很少會答不上來。「了解一切真的令人愉悅,」這位作家、演說家兼紐約特立獨行的代表人物在2010年由她的好友馬丁·斯科塞斯執導的紀錄片《公眾演講》中說道。這部紀錄片探索了她的人生和作品。 「現在,我確信人們會想,她不可能什麼都懂。但他們錯了。我什麼都懂。」 只要花點時間聽她講話,或者讀讀她那些被反覆提及的觀點——比如「禮貌的談話很少能帶來真正的平靜」,或者「根本沒有內心的平靜,只有焦慮和死亡」——你很可能也會被說服。所以,令人驚訝的是,在我們談話開始五分鐘后,我們偶然發現了一個令萊博維茨也困惑不已的現象。
「我從來沒有,也永遠無法理解,」她開口說道,「為什麼你們——我指的不是你個人,而是作為你們國家的一份子——為什麼你們總是投票給保守黨?」
現年73歲的萊博維茨如今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分享她對政治的看法,或是探討為何世上文字泛濫(「能寫出一句話或一篇文章,並不代表它就值得一讀,」她告訴我),以及她為何熱愛紐約、為何厭惡紐約,或是其他種種令她煩惱的事情。自1971年為安迪·沃霍爾的《訪談》雜誌撰寫幽默專欄以來,她以節奏明快、略帶暴躁的喜劇風格剖析世界,吸引了無數粉絲,他們為了聆聽她的演講而排起長隊。2021年,Netflix推出了七集紀錄片《假裝它是一座城市》(Pretend It』s a City),這部紀錄片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斯科塞斯執導的《公眾演講》(Public Speaking)的續集,此後,Z世代也成為了她的新晉偶像。儘管如此,萊博維茨仍然認為自己常常被人誤解。
「人們對我的一個誤解是,我刻薄。我才不是呢!我一點也不刻薄——我非常討人喜歡!」她提高音量,強調道。「不過,我的確有一點在這裡已經過時了——幾十年了——那就是我非常愛評判別人。評判別人是我清醒的標誌。我會評判每一件事。而且每個人都必須這樣做,因為對我來說,這就是我觀察世界的方式。」
如今,萊博維茨的職業可謂得天獨厚——評判和觀點是網路世界最有價值也最具爭議的商品,儘管她從未涉足過評論區。在我們正式交談之前,我模擬了一下聯繫萊博維茨的過程——撥打她的座機號碼,聽到鈴聲響起,然後等待答錄機發出咔噠聲,她才接聽。近年來,萊博維茨因為可能是整個曼哈頓唯一一個從未擁有過手機的人而備受關注,她稱之為「一個人的世界」。

2012年斯科塞斯 猶太人 和萊博維茨 猶太人 Scorsese and Lebowitz in 2012 (Getty)
她從未擁有過電腦,甚至連打字機都沒有。她寫作時,用的是一支圓珠筆,而且寫得很慢。但今天,她的公關人員的一份聲明嚴禁我們談論此事,也禁止我們談論她終生對吸煙的熱愛。我認為這很合理——萊博維茨憑藉1978年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大都會生活》一舉成名,緊接著是1981年出版的第二本,也是她最新的散文集《社會研究》(這兩本書後來合併成《弗蘭·萊博維茨讀本》)。此後四十多年來,她一直被問及寫作瓶頸——或者如她自己所稱的「寫作障礙」——以及她的下一本書何時出版。多年來,她一直把這歸咎於「懶惰」;2022年,她告訴《衛報》,她在寫作方面是個「精神錯亂的完美主義者,這讓寫作變得非常困難」。
在此期間,除了演講之外,萊博維茨(《紐約時報》曾將她比作現代版的桃樂絲·帕克)還擔任《名利場》的特約編輯和專欄作家,並時不時登上該雜誌的最佳著裝榜單。她或許同樣以獨特的風格而聞名,這使得她在紐約街頭漫步時總是格外引人注目。不知何故,她是倫敦薩維爾街裁縫店安德森和謝潑德(Anderson and Sheppard)唯一在世的女性顧客(他們為另一位女性設計服裝的是瑪琳·黛德麗),她告訴我,她擁有大約15件標誌性的西裝外套,這些外套總是搭配布魯克斯兄弟的襯衫、捲起褲腳的李維斯501牛仔褲、牛仔靴、齊下巴的黑色波波頭和玳瑁眼鏡。她也喜歡「好傢具」——對於一個擁有超過12000冊藏書的人來說,這或許是必需品。
這一切與她早年在紐約70年代藝術圈的經歷截然不同,當時的藝術圈如今已成為一種文化現象。萊博維茨從新澤西州的莫里斯敦搬到紐約,她在那裡長大,是猶太傢具裝潢師的長女。她因「莫名其妙的脾氣暴躁」被學校開除后,便將目光投向了紐約,1969年,19歲的她搬到了那裡,希望成為一名詩人。然而,為了維持生計,她不得不做計程車司機、清潔公寓以及為政治文化雜誌《變革》(Changes)銷售廣告位。《變革》由傳奇爵士作曲家兼貝斯手查爾斯·明格斯的妻子蘇·明格斯創辦。21歲時,萊博維茨開始在《訪談》(Interview)雜誌上發表專欄文章「我報道海濱」(I Cover the Waterfront),並由此開始了她對安迪·沃霍爾的公開批評。
萊博維茨二十多歲的餘生都沉浸在紐約標誌性的夜店文化中,像Max's Kansas City和Studio 54這樣的傳奇夜店吸引著藝術家、音樂家、詩人——以及所有對思想和享樂充滿渴望的人。在那裡,她與爵士樂傳奇人物杜克·艾靈頓、攝影師彼得·胡亞爾和羅伯特·梅普爾索普以及紐約娃娃樂隊等音樂人交往甚密。她最親密的朋友之一是作家托妮·莫里森,兩人於1978年相識,萊博維茨後來在《巴黎評論》中稱她為「我認識的最有趣的人之一」。
「對我來說,友誼是我最重要的關係,」她說。「友誼是我們唯一可以選擇的關係。當然,我們無法選擇家人,人們總是談論選擇和戀愛關係,但這並非事實。浪漫的吸引力,情慾的吸引力,是一種化學反應,你無法選擇它。」她看到現在的年輕人用一系列理想伴侶的特質和規則來「規劃」他們的約會生活,萊博維茨說,這完全違背了愛情的本質。「親愛的,愛情不是這樣的,」萊博維茨說道,並補充說她自稱是個「糟糕的女朋友」,因為她「對家庭生活和一夫一妻制毫無興趣」。「如果你那樣選擇伴侶,那更像是你在雇傭一個人。這就是我對浪漫的理解。但友誼,那是你可以真正選擇的。」 和弗蘭·萊博維茨做朋友是什麼感覺?「我是一個非常好的朋友。我很忠誠,也希望朋友對我忠誠。有人說,『你就像黑手黨成員一樣』;我說,『沒錯』。」
我從未想過特朗普會贏。他被房地產開發商瞧不起。你能想象道德淪喪到如此地步嗎?
萊博維茨始終忠於自己的政治信仰,自稱是「老派的新政民主黨人」,堅信經濟改革能夠縮小貧富差距。她過去曾將共和黨人描述為「無政府主義者」和「民主的破壞者」,指責他們削減公共服務、將移民問題當作替罪羊,這與她之前了解到的保守黨如出一轍——而她對保守黨也同樣不屑一顧。我們此時正值政治風雲變幻之際——距離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封口費」案開庭正好一周,未來幾個月,美國和英國都將再次步入總統大選和議會大選的行列。
她認為特朗普有可能再次當選嗎?「不,我不這麼認為,」萊博維茨說道。 「但你知道,他最終勝選的那一年,我花了整整一年時間走遍全國各地,告訴成千上萬的人他根本沒戲。我從沒想過他會贏。房地產開發商都瞧不起他。你能想象那種道德淪喪到何種地步嗎?那是我人生中最震驚的事情之一。」
四年過去了,萊博維茨對現狀依然不以為然。當她談到亞利桑那州決定恢復一項兩百多年前的法律時,語氣明顯十分惱火。這項法律禁止除危及母親生命以外的任何理由墮胎。「任何其他理由,」她特意強調道。她滔滔不絕地抨擊收入不平等作為一種政治選擇,以及基督教右翼妖魔化窮人的虛偽——「我不是耶穌專家,但我覺得食品券這種東西,耶穌自己肯定也會想到!」——她從一個令人作嘔的現象講到另一個。
除了比克圓珠筆和吸煙之外,還有一個話題被她正式列入禁區:以色列和加沙。但在其他任何話題上,萊博維茨精準的機智和恰到好處的時機,幾乎總能在每句話的結尾留下深刻的印記。只有當我們談到特朗普時(她經常會提到這個話題,以及她對共和黨的強烈反對),她的語速才會稍稍放慢。我問她,我們是不是都應該像她一樣,更有主見,更直言不諱一些。「有些人害怕說某些話,有些話確實應該害怕說,」她回答道,聲音低了下來,又補充道:「有些特朗普的支持者會去別人家門口,威脅別人。我生活在一個數百萬人擁有數百萬支槍的國家。所以,如果你在某個地方或以某種方式說了什麼,可能會招致這些人找上門來,那我肯定會害怕。如果你害怕因為說了話就被人喜歡,那就太蠢了。如果你害怕他們會開槍打死你,那倒也說得通。問題是,現在一切都太極端了,根本沒有冷靜的對話可言。」

萊博維茨出現在2021年Netflix紀錄片《假裝它是座城市》中(Netflix)
在萊博維茨居住的50年間,紐約經歷了諸多政治動蕩。當其他人沉醉於20世紀70年代波西米亞式的享樂主義時,萊博維茨初來乍到時,紐約卻是一片金融混亂和暴力橫行的泥潭。到了1975年,州工會代表開始散發名為《歡迎來到恐懼之城》的恐嚇小冊子,其中列出了九條保護個人和財物生存的秘訣,包括晚上6點以後不要在紐約外出。
與此同時,格洛麗亞·斯泰納姆和多蘿西·皮特曼·休斯正在共同創立婦女行動聯盟,而在萊博維茨的圈子裡,艾滋病疫情即將爆發。一切都徹底崩塌了。上世紀80年代,萊博維茨的許多朋友因艾滋病去世,留下了她之前所說的文化空白,而原本應該留下一代才華橫溢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
2018年,萊博維茨在接受《Inside Hook》雜誌採訪時表示,她成長於一個「同性戀不存在」的年代,但如今她已成為酷兒偶像,儘管有時她並不情願(她堅稱自己從未為同性婚姻奔走呼籲,並略帶諷刺地補充道:「我擔心的是它會變成強制性的」)。不過,她對當前圍繞跨性別權利「驅動政治」的持續討論感到不滿。「實際上,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會成為一件大事,」她說,「因為它實際上隻影響到極少數人。」
「這沒什麼危險的。我介意的是有人帶著槍到處走。但除此之外,你想幹什麼都行。告訴我該怎麼稱呼你,我就怎麼稱呼你……如果你不傷害別人,我就不明白(這一切到底是為了什麼)。再說一遍,這太極端了。」
她補充道,「這件事實際上除了當事人之外,對任何人都沒有影響。所以你為什麼要在意?你知道,你還不如去關注一下不公平的稅收結構。關注一下——關注一下非法污染以及各種各樣逍遙法外的事情,這些才是真正影響到每個人的。」
萊博維茨將右翼對跨性別者權利的政治參與比作故意將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提交給美國選民投票,「因為這會拉攏共和黨人」。現在,她告訴我,「他們已經從同性婚姻合法化轉向了跨性別者權利。因為這會激怒某些人。」
臨別之際,我問萊博維茨今天剩下的時間有什麼安排。她說,在接受完更多採訪后,她要坐下來付賬。「我知道大家都用……呃,該怎麼說呢?網上支付。但我不用。我喜歡拿著支票簿坐下來。我想確切地知道『花了多少錢?』,以及『錢都花到哪兒去了?』」不知怎的,就像她性格和生活方式的其他方面一樣,這讓人感到安心。
像勒博維茨這樣擁有堅定不移的自信的人寥寥無幾,她每個十年都堅持不按常理出牌;更少有人能像她那樣,完全基於真實的觀察而非屏幕前精心打造的生活版本來發言。勒博維茨當然是對的——她並不刻薄,她很可愛!但她的生活方式卻令人耳目一新。她是個盧德分子,但她對科技的排斥遠不止於此——這是一種拒絕順從、拒絕為了融入而扭曲自己的態度。我們其他人是否在這個並不真正為我們服務的世界里逆來順受?誰知道呢。弗蘭·勒博維茨或許知道。
【對這篇報道的幾個評論】
Candyblossom
2024年5月20日
那麼,這位自詡愛評判他人的女士,為何對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為卻沒有任何評判呢?難道她不想讓別人知道她是種族滅絕的支持者嗎?
CScarlett 回復。
回復 Candyblossom
她解釋說,是因為那裡有很多人持有槍支。你憑什麼指望她對此有看法?就因為她是猶太人?依我看,她對以色列一直沒什麼發言權——她只是個碰巧也是猶太人的紐約人。
langejames
2024年5月20日
但是,如果我們能讓你相信這件事影響到每個人,我們就能獲得更多關注。
Rachel
瑞秋
完全同意,生理女性在各個層面都受到那些想成為女性的男性的威脅!
可惜的是,我們都渴望一些我們無法擁有的東西。在這個時代,如果我們不喜歡自己的鼻子,我們可以做整形手術;如果我不喜歡自己的身材,我也可以做整形手術。
可悲的是,科學被用來改變我們,而不是幫助我們接受真實的自己,並讓我們過上最好的生活。
如果我生來是黑人,或者生在中國,但我不喜歡自己的膚色,那麼我們的種族和基因是無法改變的!
你就是你!想怎麼穿就怎麼穿,想怎麼做就怎麼做,但請不要侵犯生理女性的領地,也不要試圖與我們競爭。
WellActually
2024年10月20日
回復 Vagablond
太好了。如果沒人害怕跨性別者,那就沒有理由不管好自己的事。
我注意到你試圖散布一種錯誤的說法,即跨性別女性=前罪犯,並且每個跨性別者都「對女性構成威脅」。再次強調,跨性別者對我們女性沒有威脅。坦白說,如果你連只想安安靜靜地花點錢的人和心懷不軌的人都分不清,那我只能說問題出在你身上。
WellActually
回復 Vagablond
你還忽略了跨性別男性的存在,也就是出生時被指定為女性,但認同並以男性身份生活的人。他們通常看起來像男性。如果你強迫人們按照出生時被指定的性別使用公共設施,那麼他們就只能使用女廁了。
如果你關於順性別男性性侵犯者可能假裝成跨性別者以進入女廁所的說法屬實,那麼如果人們必須按照出生性別使用相應的設施,他們就更容易假裝成跨性別男性了。
弗蘭·勒博維茨在弗吉尼亞劇院吸引全場目光

佐伊·基德,特約撰稿人 • 2025年10月27日
弗蘭·勒博維茨在弗吉尼亞劇院吸引全場目光
圖片由布里吉特·拉科姆提供
周五,弗吉尼亞劇院舉辦了「與弗蘭·勒博維茨共度良宵」活動,這是一場純粹的喜劇盛宴。勒博維茨數十年來一直從事寫作、評論和幽默創作,她毫不掩飾地分享著自己對世間萬物的看法和見解。
此次活動由2025年科羅拉多大學驕傲節主辦,因為勒博維茨自踏入文壇以來一直是女同性戀的偶像。當地書店簡·亞當斯書店也贊助了此次活動,並提供了勒博維茨的著作《弗蘭·勒博維茨讀本》用於簽售會。演出結束后,排隊等候與她見面的隊伍排得老長,甚至延伸到了劇院的多個出口。
節目開場前30分鐘,安排萊博維茨與當晚主持人艾米·佩恩進行對話。她們暢談了馬丁·斯科塞斯的電影製作、紐約市長選舉以及她對中西部地區不滿之處等話題。
接下來是與觀眾的互動環節,佩恩鼓勵觀眾直接向她提問。根據萊博維茨的要求,現場沒有為觀眾提供麥克風,他們必須大聲說話,以便她能聽見——她已經75歲了。
在回答完第一個問題后,萊博維茨宣稱她的觀點從未改變,如果她說過一件事,她還會再說一遍。
「我特別喜歡她說她從未改變過自己的觀點,因為她總是對的,」香檳縣居民丹妮特·霍姆斯說道。
粉絲們發現,萊博維茨有一種特別而迷人的方式,她總是表現得極其消極和好鬥,但同時又非常幽默。她展現出的堅定和自信,即使她的觀點非黑即白,人們仍然會來聽她演講。
「我認為每個人都需要像弗蘭·萊博維茨這樣的人,」來自密蘇里州聖路易斯的艾米·肯尼利說道,她特地驅車前往香檳縣觀看萊博維茨的演講。「她太機智了——她太聰明了。我都快要熱淚盈眶了,但在這個國家如今的境況下,你可以坐在這裡,暫時忘卻正在發生的一切。」
活動伊始,萊博維茨就自嘲自己「一點也不開明」,而且非常愛評判別人,以至於小時候就夢想成為最高法院大法官。緊接著,她又說現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們令人不齒,她絕不會帶著法槌踏進白宮的法庭。
由於她對幾乎所有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許多觀眾都向她提問,詢問她對美國政治以及現任政客的看法。她深入探討了自己對美國當前政治局勢的看法,並發表了一些滑稽甚至有些離奇的言論。
她一本正經地看著觀眾,說她相信唐納德·特朗普、羅納德·里根和喬治·W·布希真的不識字。觀眾頓時哄堂大笑。
「我認為她的幽默水平堪比任何一位脫口秀演員,因為她講故事講得精彩,而且說的每句話都妙趣橫生,」霍姆斯說道。
儘管萊博維茨的發言逗得觀眾哈哈大笑,但一些觀眾仍然認真思考了她的話。她談到了許多熱門話題,例如政治無能和槍支暴力,但最引人關注的還是美國的移民問題。
「我不在乎那些為了逃避困境而來到這裡,卻還沒完成合法身份手續的人,」香檳縣居民梅蘭妮·馬加拉說道,「這與我無關。真正讓我感到不安的是現在正在發生的殘酷現實。」
萊博維茨從不畏懼就任何話題發表自己的看法。幾十年來,她一直直言不諱,即使某些觀點頗具爭議,她也會毫不客氣地回擊任何挑戰她的人。
為了概括萊博維茨的諷刺風格和當晚的氛圍,一位觀眾問她,如果有什麼能讓她感到希望,那是什麼?「如果我想到了,我會打電話給你,」萊博維茨回答道。
再看一位「特立獨行」比金斯伯格男人氣N倍的自由派猶太女大嘴---弗蘭·勒博維茨

2011年的勒博維茨 (猶太人,75歲,女同性戀,高中被開除,被推出代表Z時代的偶像)
原名:弗朗西絲·安·勒博維茨
1950年10月27日(75歲)
美國新澤西州莫里斯敦
職業
作家、公共演說家、演員
國籍:美國
體裁:散文
代表作:《大都會生活》(1978)
《社會研究》(1981)
網站
franlebowitz.com
弗朗西絲·安·勒博維茨(/ˈliːbəwɪts/;1950年10月27日出生)是一位美國作家、公共演說家和演員。她以對美國社會生活的諷刺性評論而聞名,這些評論深受她對紐約都市生活的敏銳感知以及與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紐約藝術界眾多傑出人物的交往的影響,其中包括安迪·沃霍爾、馬丁·斯科塞斯、傑羅姆·羅賓斯、羅伯特·梅普爾索普、大衛·沃納羅維奇、坎迪·達林和紐約娃娃樂隊。
勒博維茨憑藉其著作《大都會生活》(1978)和《社會研究》(1981)而聲名鵲起,這兩本書於1994年合併為《弗蘭·勒博維茨讀本》。她曾是馬丁·斯科塞斯執導的兩部作品的主角,分別是HBO紀錄片《公眾演講》(2010)和Netflix紀錄片系列《假裝它是一座城市》(2021)。
《紐約時報》稱勒博維茨為當代多蘿西·帕克。
早年生活和教育
萊博維茨出生於新澤西州莫里斯敦,並在那裡長大。她有一個妹妹,名叫艾倫。她的父母是露絲和哈羅德·萊博維茨,他們擁有一家名為「珍珠軟墊傢具」的傢具店兼軟墊傢具工坊。 她從小就熱愛閱讀,甚至會在課堂上偷偷看書,而忽略家庭作業。萊博維茨形容她的「猶太身份是民族的、文化的,或者現在人們怎麼稱呼它都行。但它不是宗教性的。」 她從7歲起就成為了一名無神論者。她沒有舉行成人禮,但一直上主日學校直到15歲,並接受了堅信禮。
萊博維茨的學習成績總體來說不太好,尤其是代數,她掛了六次。她稱之為「他們給我展示的第一件我完全無法理解,也絲毫沒有興趣理解的事情」。 她曾在一家卡維爾冰淇淋店工作。 她的成績非常差,以至於她的父母把她送進了威爾遜學校(現已關閉,其校舍已被克雷格學校收購),這是一所位於山湖鎮的私立女子聖公會學校。在那裡,她的成績略有提高,但她難以遵守校規,最終因「無緣無故的桀驁不馴」而被開除。[15][20]她還因為偷偷溜出莫里斯敦高中的啦啦隊集會而被停學。
青少年時期,萊博維茨深受詹姆斯·鮑德溫的影響:「詹姆斯·鮑德溫是我在電視上看到的第一個說話方式如此獨特的人——我的意思是,他是第一個我聽到的知識分子……我當時簡直驚呆了。這促使我開始閱讀他的作品。」她也喜歡觀看戈爾·維達爾和威廉·F·巴克利的電視節目,儘管她並不認同巴克利的觀點。
早期經歷
萊博維茨被高中開除后,獲得了高中同等學歷證書。18歲時,父母把她送到紐約州波基普西的姨媽家居住。她在那裡住了六個月,然後於1969年搬到紐約市。她的父親同意支付她在紐約市頭兩個月的房租,條件是她必須住在僅限女性入住的瑪莎·華盛頓酒店。之後,她暫住在紐約朋友的公寓和波士頓的大學宿舍里,靠幫學生寫論文維持生計。20歲時,她在西村租了一間公寓。為了養活自己,她做過清潔工、司機、計程車司機和色情小說作家。 萊博維茨拒絕當服務員,因為她聲稱很多餐廳都要求員工必須與經理髮生性關係才能被錄用,而且她「不能為了錢對人微笑」。
21歲時,萊博維茨在《變革》(Changes)雜誌工作,這是一本「關注激進時尚政治和文化」的小雜誌,由查爾斯·明格斯的第四任妻子蘇珊·格雷厄姆·翁加羅創辦[29]。她負責銷售廣告位,之後又撰寫書評和影評。安迪·沃霍爾隨後聘請勒博維茨擔任《訪談》雜誌的專欄作家,她撰寫了兩個專欄:「最差中的最好」(The Best of the Worst),專門評論爛片;以及「我報道海濱」(I Cover the Waterfront)。之後,她又在《少女》(Mademoiselle)雜誌工作了一段時間[31]。在此期間,她結識了許多藝術家,包括攝影師彼得·胡亞爾(Peter Hujar,兩人於1971年相識)和羅伯特·梅普爾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後者經常贈送她照片,其中許多照片在20世紀70年代被她丟棄了。
1978年,她的第一本書《大都會生活》(Metropolitan Life)出版。這本書收錄了她主要發表在《少女》和《訪談》雜誌上的幽默散文,標題包括「沒有大學也能成功」(Success Without College)和「關於幾個詞的幾句話」(A Few Words on a Few Words)。她經常以一種冷幽默的口吻,詳細描述那些令她感到惱火或沮喪的事情。該書出版后,萊博維茨成了當地名人,經常出入聖路易斯街。
1978年,她的第一本書《都市生活》(Metropolitan Life)出版。這本書是一部喜劇散文集,主要收錄了她發表在《Mademoiselle》和《Interview》雜誌上的散文,標題諸如《不上大學也能成功》(Success Without College)和《關於幾個詞的幾句話》(A Few Words on a Few Words)。她經常以一種冷幽默的口吻,詳細描述那些令她感到惱火或沮喪的事情。這本書出版后,勒博維茨成為了當地名人,經常出入Studio 54夜總會,並定期出現在電視脫口秀節目中。之後,她又出版了《社會研究》(Social Studies,1981),這是另一部喜劇散文集,主要收錄了她發表在《Mademoiselle》和《Interview》雜誌上的散文,探討了青少年、電影和客房服務等話題[36]。多年後,《弗蘭·勒博維茨讀本》(The Fran Lebowitz Reader,1994)出版,其中收錄了這兩本書。
寫作瓶頸與公眾形象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萊博維茨就因其長達數十年的寫作瓶頸而聞名。 她上一部出版的作品是《查斯先生和麗莎·蘇遇見熊貓》(1994),這是一本兒童讀物,講述了生活在紐約市的大熊貓渴望搬到巴黎的故事。此後,萊博維茨曾參與過多個未完成的寫作項目。其中包括《財富的外在標誌》,這是一部遲遲未能完成的小說,據稱講述的是想成為藝術家的富人和想成為富人的藝術家之間的故事。另一部作品《進步》的節選於2004年發表在《名利場》雜誌上,但至今仍未完成。在談到寫作瓶頸時,她說:「我的編輯——每次我介紹他時,他總是說『這是城裡最輕鬆的工作』——他說我寫作時的癱瘓是由於我對文字的過度敬畏造成的,我想這大概是真的。」

萊博維茨(右)與哈羅德·奧根布勞姆、華萊士·肖恩和黛博拉·艾森伯格在2011年布魯克林書展的小組討論會上。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萊博維茨主要依靠演講維持生計。(ebowitz (right) with Harold Augenbraum, Wallace Shawn and Deborah Eisenberg during a panel discussion at the 2011 Brooklyn Book Festival. Since the 1980s, Lebowitz has largely supported herself with speaking engagements.)
由於寫作瓶頸,萊博維茨主要依靠電視節目和演講維持生計。她曾說過:「這就是我一生所渴望的。人們徵求我的意見,而且不允許打斷我。」[39] 她以公眾演講者的身份巡迴演講,由史蒂文·巴克萊經紀公司代理。此外,她曾多次亮相大衛·萊特曼的深夜脫口秀節目[13],並在2001年至2007年間在電視劇《法律與秩序》中飾演法官詹妮絲·戈德堡。她至今仍從事新聞寫作;自1997年以來,萊博維茨一直是《名利場》雜誌的特約編輯和專欄作家。
通過公開露面,萊博維茨吸引了更廣泛的受眾,他們也逐漸熟悉了她獨特的風格。她以機智的妙語和對各種話題的敏銳觀察而聞名,包括紐約市、中產階級化、藝術、文學和政治。她通常穿著男士西裝外套(由薩維爾街的安德森·謝潑德定製)、白襯衫、牛仔靴、李維斯牛仔褲和玳瑁眼鏡。她經常談起她珍愛的1979年款珍珠灰Checker計程車,這是她唯一擁有過的車,她稱之為「我一生中唯一一段忠貞的感情」。2007年9月,萊博維茨在《名利場》雜誌第68屆年度國際最佳著裝榜單中被評為年度最具時尚感的女性之一。 一年一度的FranCon活動旨在慶祝萊博維茨的時尚品味,參與者都會穿著她標誌性的服裝。
萊博維茨還以其龐大的藏書而聞名,總共藏書1萬冊,其中至少有一架書架專門擺放肥皂雕刻書籍。 此外,她還拒絕使用許多科技產品,包括手機和電腦。萊博維茨煙癮很大,但她也是吸煙者權益的倡導者。自19歲以來,她就再也沒有碰過毒品或酒精,她說這是因為她在19歲時就已經達到了「終生用量」。
2010年,萊博維茨出現在HBO紀錄片《公眾演講》(Public Speaking)中,這部由馬丁·斯科塞斯執導的紀錄片讓她被新一代觀眾所熟知。該片包含對她的採訪以及她演講的片段。 2010年11月17日,她時隔16年重返大衛·萊特曼的《深夜秀》(Late Show with David Letterman),宣傳這部紀錄片。她談到了自己多年來的寫作瓶頸,並戲稱之為「寫作障礙」(writer's blockade)。萊博維茨還在斯科塞斯2013年的電影《華爾街之狼》(The Wolf of Wall Street)中客串出演了一位法官。她與斯科塞斯再次合作,推出了2021年Netflix的紀錄片《假裝它是一座城市》(Pretend It's a City),斯科塞斯在片中採訪了她,談論紐約市和其他話題。
觀點
紐約市
萊博維茨一直對紐約市的士紳化和文化變遷持批評態度。她解釋說,「老紐約」和「新紐約」的主要區別在於金錢文化的影響和主導地位。雖然紐約一直都是一座消費高昂的城市,但即使不富裕的人也能住在曼哈頓,「不必每時每刻都為錢發愁」。這主要是因為,除其他原因外,「以前有無數糟糕的工作。現在這種情況已經不存在了。我的意思是,我可能某天下午醒來發現自己身無分文——我指的不僅僅是房租,而是我名下的錢——但我知道到一天結束時,我就會有錢了。」
她曾批評紐約市長魯迪·朱利安尼和邁克爾·布隆伯格,認為他們讓紐約變得更加「郊區化」,並加速了曼哈頓的士紳化進程。她也批評紐約市的大量富人,因為她認為他們不創造任何價值,只會消費。 談到布隆伯格,她說:
「我反對有錢人從政。我認為他們不應該被允許從政。有錢人從政很糟糕,這對除了富人以外的所有人都不利,而且富人不需要任何幫助。」每當有人說「哦,他的錢都是他自己掙的」,我總是說同樣的話:「沒人能一夜暴富. 時薪只有10美元,卻能偷到10億美元。」
談到朱利安尼的執法政策,她說:「朱利安尼當市長的時候,平均每五分鐘就有一名手無寸鐵的黑人男子被槍擊背部。」萊博維茨厭惡紐約市遊客眾多,稱20世紀80年代將紐約市打造為旅遊目的地的舉措「簡直糟糕透頂」。她指出旅遊業是紐約住房短缺的原因之一,因為酒店比公寓樓建得多,並描述了城市經濟過度依賴旅遊業帶來的負面影響:「你不可能把這些鄉巴佬大批引到城市中心,而不對城市造成影響。」
談到紐約的無家可歸危機,她說道:「任何一個走在這座富裕城市的紐約人……你什麼都聽不見,因為金錢的喧囂太過震耳欲聾,看到街上的人,卻不覺得這是國家的恥辱,是城市的恥辱。」
艾滋病的影響
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萊博維茨的許多同性戀藝術家朋友,包括彼得·胡亞爾、保羅·塞克和大衛·沃納羅維奇,都死於艾滋病。她曾探討過紐約的艾滋病疫情對美國文化的影響。她尤其談到了失去一代才華橫溢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后留下的文化空白。這些人不僅創作藝術和知識文化,他們本身也是熱情洋溢的受眾,孕育了這些文化。正如她在2016年的一次採訪中所解釋的那樣:
「沒有同性戀者,文化是什麼?這裡是美國,文化又是什麼?不僅僅是紐約。艾滋病徹底改變了美國文化……隨著艾滋病的爆發,整整一代男同性戀者幾乎在短短几年內全部離世。尤其是我認識的那些人。最早死於艾滋病的是藝術家。他們也是最有趣的人……那些真正了解他們的受眾也隨之消逝,不再真正存在……人們的知識存在巨大的空白,而且不再有相關的語境。」
1987年,萊博維茨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艾滋病對藝術界的影響》的文章。
女權主義

萊博維茨出席2010年翠貝卡電影節
萊博維茨曾被稱作「與『向前一步』女權主義截然相反的人物」。 她在2019年的一次採訪中說道:
「如果(女權主義)真的有效,就不會有女權主義了。有些事情確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現在女孩的生活比我小時候好太多了。根本沒法比。現在好太多了,但同時又很糟糕。這足以說明以前的生活是什麼樣的,好嗎?」
在另一次採訪中,她說道:「我當時沒太關注女權主義,主要是因為我從來沒想過它會奏效。不幸的是,我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的。」她還說過:「現在女孩的成長方式截然不同……我小時候,如果你想做某件事卻不被允許,通常的答案是:因為你是女孩。」
談到「我也是」(#MeToo)運動,她說:
「我從沒想過這種情況會改變。從夏娃到八個月前,做女人一直都是一樣的。所以我從沒想過它會改變。真的。我可以告訴你,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令人驚訝的事情之一。最先被抓的四十個男人——我幾乎都認識。」
政治
萊博維茨自認為是自由派民主黨人,經常批評溫和派民主黨政治家和政策。多年來,她一直是共和黨的激烈批評者,最近更是抨擊唐納德·特朗普總統。 她曾表示,特朗普吸引選民的手段是「純粹的種族主義」,並將特朗普的競選集會比作三K黨和喬治·華萊士的集會。她曾稱特朗普為「卑鄙的騙子」、「愚蠢」、「懶惰」,還說他「有點瘋,但主要是蠢」。談到特朗普2016年的當選,她說:「太可怕了。我至少在一個月內都深受情緒影響。我的憤怒情緒一直很高,現在更是達到了頂點。」 她開玩笑說:「如果說這一切(特朗普當選)有什麼好處的話,那就是它讓特朗普離開了紐約。」
萊博維茨也批評過許多其他政治人物。她曾表達過對比爾·柯林頓的反感,認為他將民主黨推向了右翼,她說:「在我看來,他就像個共和黨人……當他簽署福利法案時,我簡直要瘋了。他是一位成功的溫和派共和黨總統。」萊博維茨也曾表達過對伯尼·桑德斯的厭惡,她一度稱他為「一個令人難以置信地煩人、自戀的老頭」,認為他搶走了她支持的候選人希拉里·柯林頓的選票。 她經常把羅納德·里根描述為「愚蠢總統的模板」,並說「在里根之前,人們根本不知道總統也可以很愚蠢。」
萊博維茨曾表示,她認為第二修正案被誤解了,它保障的是個人組建民兵的權利,而不是持有武器的權利。關於槍支權利的爭論,她曾說過:
「這些熱愛槍支的人到底是誰?」這些既熱愛特朗普又熱愛槍支的人,是我這輩子見過的最膽小的人……我本來也可以弄到槍,但我從來沒弄過。我18歲的時候是個身無分文的女孩,住在危險的城市裡,但我從來沒有像這些生活在德克薩斯州、生活在恐懼之中的男人那樣害怕過。
2019年5月,萊博維茨在比爾·馬赫的脫口秀節目《實時》中開玩笑地建議,特朗普應該遭受和《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賈邁勒·卡舒吉一樣的命運。中央情報局和其他多個情報機構認為,卡舒吉是被沙特特工奉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之命折磨致死的。 她在節目後期收回了這番言論。
個人生活
萊博維茨對自己的個人生活毫不避諱,她是一位女同性戀者。她曾公開表示自己在戀愛關係中遇到困難。 2016年,她曾說過:「我是世界上最棒的女兒。我是一位很棒的親戚。我相信我是一位很棒的朋友。但我卻是一位糟糕的女朋友。我一直都是。」
萊博維茨是托妮·莫里森多年的摯友。
她「出了名的抗拒科技」,沒有手機、電腦或打字機。
萊博維茨的右眼失明,這是先天性的。
作品
影視作品
電影
年份 片名 角色 備註
1990 《巴黎在燃燒》 本人 紀錄片
2010 《公眾演講》 本人 HBO 紀錄片
2013 《華爾街之狼》 尊敬的薩曼莎·斯托格爾 故事片
2014 《基要之河》 嘉賓 [本人][75] 故事片
2014 《關於蘇珊·桑塔格》 本人 HBO 紀錄片
2016 《梅普爾索普:看看照片》 本人 紀錄片
2017 《安德烈福音》 本人 紀錄片
2018 《永遠在卡萊爾》 本人 紀錄片
2019 《托妮·莫里森:我之碎片》 本人 紀錄片
2019 《書商》 本人 紀錄片
2020 《沃納羅維奇:去你媽的同性戀》 本人 紀錄片
2023 《又名周先生》 本人 HBO 紀錄片
電視劇
年份 片名 角色 備註
1980大衛·萊特曼秀(本人)- 客串:1980年6月30日
1982-10 大衛·萊特曼深夜秀(本人)- 客串:15集
1982 邁克·道格拉斯秀(本人)- 客串:大衛·哈塞爾霍夫/弗蘭·勒博維茨
1994-10 查理·羅斯訪談錄(本人)- 客串:6集
1994-2000 柯南·奧布萊恩深夜秀(本人)- 客串:7集
2001-2007 法律與秩序:珍妮絲·戈德堡法官(本人)- 12集
2006 法律與秩序:犯罪傾向(本人)- 客串:「骨瘦如柴」(To the Bone)
2010-2013 吉米·法倫深夜秀(本人)- 客串:3集
2015-2021 吉米·法倫今夜秀(本人)- 客串:8集
2015-2024 比爾·馬赫實時秀(本人)- 客串:9集
2021 假裝一切都好《城市之聲》(City Herself)製片人;Netflix紀錄片系列[76]
2021年《賽斯·梅耶斯深夜秀》(Late Night with Seth Meyers)本人 - 客串:比爾·哈德爾/弗蘭·勒博維茨
2021年《Ziwe》本人 - 客串:「55%」
參考書目
《大都會生活》(Metropolitan Life),達頓出版社,1978年。ISBN 978-0-525-15562-1
《社會研究》(Social Studies),蘭登書屋,1981年。ISBN 978-0-394-51245-7
《弗蘭·勒博維茨讀本》(The Fran Lebowitz Reader),復古出版社,1994年。ISBN 978-0-679-76180-8
《查斯先生和麗莎·蘇遇見熊貓》(Mr. Chas and Lisa Sue Meet the Pandas),克諾夫出版社,1994年。ISBN 978-0-679-86052-5
勒博維茨,弗蘭;沃霍爾,安迪 (2004)。布蘭特,桑德拉·J.;西斯奇,英格麗德(編)。《安迪·沃霍爾訪談錄:流行文化的水晶球》。第7卷:弗蘭·勒博維茨:我報道海濱。巴黎:Edition 7L出版社。ISBN 3865210236。OCLC 314795464。原件存檔於2021年1月16日。[77]
《財富的外在標誌》(未完成,未出版)[78][79][80]
《進步》(未完成,未出版),紐約:克諾夫出版社,2003年,OCLC 52860152,ISBN 9781400041367[78]
- [11/07]最新!華人父親萬聖節當街被槍搶,年幼女兒目睹全過程!
- [11/07]紐約「當選」「穆斯林」猶太小市長的秘密資金來自全球主義億萬富翁!
- [11/08]謝幕人生滋味濃::李政道仰望葉企孫 楊振寧不如胡蘭成?
- [11/08]【直播】戰爭部長赫格塞斯在國家戰爭學院發表演說
- [11/09]糊口不易 讀者熱議 清潔女上錯門 中槍死夫前
- [11/10] 特立獨行 結局不同
- [11/10]【老外熱議】佛蒙特東北美女大媽一隻餃子熱賣2.5美元是啥樣的?
- [11/11]政府停擺內情發展:川普大戰醫保公司
- [11/12]老兵節放話!川普痛斥外國人無功享福利 退伍兵有難卧錐地
- [11/16]萬斯: 十年政變浩劫 一朝審判光復
- [11/16]日本紅歌也瘋狂---高市早苗~紅色誓言~」
- [11/16]歲寒的基因
- [11/17]你們跪吧,我站著
- 查看:[change?的.最新博文]
- 查看:[大家的.最新博文]
- 查看:[大家的.家庭新聞]
評論 (0 個評論)
change?最受歡迎的博文
其它[家庭新聞]博文更多
- change?:生命奇迹小勝大? 印富蜂難 vs 印機空難
- change?:尹錫悅的與眾不同與父親的關係
- 8288:斷舍離
- 8288:《當我要去養老院的時候》
- change?:亞大華授槍殺妻 家暴頻劇兒不奇
- change?:奧巴馬弟弟寫書揭其使用合成物再造
- 8288:讓世界重新變得未知的工具,還是妥妥的碎鈔機?[轉貼]
- 重返伊甸:有情人終成眷屬
- 澳洲雪梨子:我親歷的民俗靈驗
- 8288:華人美國挖野菜,吃罰單?
- Shelwen:不想像父母一樣
- 海外思華: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 紅杏桃子245:人生悲劇,幾個月內一家三代都沒了
- 8288:有錢≠值錢,三位老人的故事,養老金很有必要
- 紅杏桃子245:周末請聽歌曲 「這一生還是你最好」
- 紅杏桃子245:不願自食其力的後果---「可怕的老美朋友」 (續)
- 8288:北京突然宣布:再見了,商品房!
- 加家龍哥:這個流浪漢,在我家門前連坐好多天都不走,他竟然還是沖著我家來的. (視頻)
- 8288:恐怕有一天我們不得不拍護工的馬屁
- 8288:七十歲前和七十歲后,完全是兩個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