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帖最後由 硨磲大爺 於 2016-11-29 04:06 編輯

撰文:高波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社會主義論戰被當作是「五四運動過後政治思想論壇上一場參加人數最多、歷時最長的大辯論」,且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敘述中極其重要的一環,被視為其在思想與組織兩方面「從自發走向自覺」的關鍵事件。論戰由張東蓀1920年11月6日在《時事新報》上發表的一篇不到600字的時評(《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所引發。該時評以他之前與羅素等人赴湖南演講為背景,強調這次內地之行讓他發現了中國內地的貧窮,並認為各種外來主義(尤其是社會主義)與中國當下現實並不相關,因此要放棄談主義而主張「發展富力」,以讓內地人能夠過上「人的生活」。此文被認為是以曲折的方式否定社會主義並主張資本主義,引起了上海等地的早期共產主義者、國民黨員以及趨新青年的激烈回應。論戰持續數年,深刻地影響了五四后新勢力的分野以及中國早期社會主義運動的走向。
1
論戰主題與各方觀點
如前所述,張東蓀引發論戰的時評,文章不長,觀點也不複雜,核心在於把中國內地的情形與各種西方的「主義」對立起來,反對當時人人「談主義」的局面。該文被放在《時事新報》第二張第一版發表,就位置而言,並不及首張頭版的社論來得重要,且文中並沒有明確提到資本主義的問題(甚至就沒有出現資本主義的字樣)。但從論戰一開始,邵力子、李達與陳望道都對該文高度重視,並都把張東蓀主張不談主義而發展富力當作是要主張資本主義。 由此,中國與資本主義的關係——當時的中國是否有資本主義,或是否需要經過一個「資本主義階段」的問題——從一開始就進入了論戰的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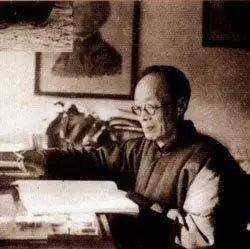
張東蓀
張東蓀隨後的回應多少已受到這些最初批評的制約:他不得不對資本主義表明態度。他聲明自己主張為了發展實業,必須對資本主義「長期的忍耐」。在他看來,問題並不在於資本主義是否正當,而在於當時的中國沒有「拒絕資本主義的能力」,資本主義「不可逃避」。 因為「中國只有幾個交通的商埠有工人,縱使在這幾個商埠有什麼舉動,也決不能影響全國。結果至多也不過做到一個半生不熟的變化,好像辛亥一樣。」 換言之,因為資本主義階段不可跨越,因此,他雖然不歡迎資本主義,但卻準備接受它。由此更進一步,梁啟超等人主張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壓迫下,必須以發展富力的名義支持民族資本家的發展。這實際上是半正式提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核心問題——民族資本家的問題。
面對中國的「資本主義階段」與民族資本家的問題,當時的社會主義者不願意凸顯中國的特殊性,因此傾向於對二者均持否定態度。其辯護策略,則是強調資本主義階段可以跨越,或乾脆認為中國此時已有了足夠多的資本主義。即要麼是反對「愛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結合」,因為「勞動者沒有祖國」, 要麼放寬經典馬克思主義對於資產階級的嚴格定義,主張出租土地或僱工的農民就是「無數的小資本家」。
大體上,在這次論戰中,梁啟超、張東蓀等人強調中國與西方從政治到文化的區隔,並因此認為必須對中國的特殊情況加以區別對待;而早期社會主義者則竭力拉近中國(尤其是廣大內地)與世界的距離,認為二者在政治與經濟上都必須被當作一個整體,用李大釗的話說就是:「中國國內的勞資階級間雖未發生重大問題,中國人民在世界經濟上的地位,已立在這勞工運動日盛一日的風潮中,想行保護資本家的制度,無論理所不可,抑且勢所不能。」
在這種心態下,此時的社會主義者多表示出一種特別的擔心,那就是若在中國內地造成資本主義,將會增加他們想象中的人民的痛苦。他們因此常用「病」與「葯」作比喻,認為「一定要把中國現在的病症移做資本主義的病症而後照西洋的原方用藥」,只是「庸醫」乾的事——這一比喻隱含著早期社會主義者心目中內地形象的兩面。疾病總對應著健康,若果真「資本主義是社會的病」, 則中國內地前資本主義的狀態多少就可被看作是「健康」的;但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內地是極端落後而急需改造的。
問題在於用什麼來改造這一「健康」而又「落後」的內地。對早期社會主義者來說,相對正面化的資產階級形象是對其社會主義理想重大的威脅。比起這些多為青年學生的早期社會主義者,清末民初就活躍於政壇的梁啟超、張東蓀等人,受晚清以來實業風潮的影響,對資本主義與民族資本家都更了解與親近,他們對本國資本主義「長期的忍耐」是為了以此抵抗世界資本主義的威脅,顯示了比早期社會主義者更明顯的國族意識,並表達出對之前新文化運動強烈的世界主義的一種修正與反撥。反過來,雖然「反帝」是之後「國民革命」的兩大口號之一,但大多數早期社會主義者因其與新文化運動的緊密聯繫,更熟悉的仍是「反傳統」,將中國的困境主要歸咎於外國,多少會讓他們覺得是在減輕傳統的罪責,且與其外向的世界主義認同也有著衝突。
不過,在論戰中,比起這種心態層面的對立,更值得注意的倒是雙方觀點與思想資源的趨同。雖然梁啟超、張東蓀等人被認為是要在中國主張資本主義,但就否認資本主義的價值而論,他們與早期社會主義者並無二致。事實上,不管是出於本意還是順應時勢的自我禁抑,當時的趨新知識分子在其公開發言中幾乎無人真正對資本主義持肯定態度(五四后的社會改造運動一大共識就是對資本主義的否定),社會主義更是已如同清末的「立憲-革命」以及民初的「法政」一樣,成了「很時髦的一種『口頭禪』」。 雙方所爭論的, 更多仍在於是否需要立刻抑制甚至消滅資本主義這一手段層面的問題。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的既存研究對梁啟超、張東蓀的評價前後變化很大,但大致都承認二人的觀點中多少包含著馬克思主義的成分(越往後肯定的程度越強)——他們主張先發展富力再談制度變革問題,多少切合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馬克思主義觀點;認為資本主義在當時的中國尚具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也離唯物主義的歷史階段論並不太遠。可以說,正是其思想方式與馬克思主義的符合,才激起了早期社會主義者的反對。張東蓀等人不僅挑戰了他們對中國現實的理解,更挑戰了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他們反應則是指責張東蓀等人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似是而非」,「最易淆惑人心」,因此「他們是社會主義的障礙,是我們的敵人。」 這種措辭顯示了他們當時所感到的壓力。
反過來,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的既存研究也大都注意到,在論戰中,是早期馬克思主義者而非他們的反對者在對該主義施以更加變通甚至是片面的解釋(且越往後越傾向於明確指出其不足)。如面對中國內地與「資本主義階段」的距離,早期社會主義者大都強調精神對社會變革的重要性,如李季就強調馬克思與恩格斯都只是「圓顱方趾的人類,並不是什麼『神』」,因此對馬克思主義不可「孔趨亦趨,孔步亦步」, 李達則說「在中國運動社會革命的人,不必專受理論上的拘束,要努力在實行上去做。」 強調不可墨守馬克思主義,顯示了此時他們心目中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國情的距離。李季指責張東蓀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階段論論證其主張不過表明他是「懂得西文的新頑固」, 就清晰地顯示出他試圖為自身對馬克思主義的變通解釋尋找心理平衡的心態。
對論戰參與者階級屬性的探討當時也已出現。在論戰中,雙方互相質疑對方代表中國廣大人民發言的資格。張東蓀被攻擊為是不敢明白主張資本主義的「自欺欺人的偽善者」, 為暗示擔任報館主筆的他就處在革命對象的位置,陳獨秀在說明中國存在無產階級時,就以報館的排字工為例。張東蓀則直接回擊說:「先生謂報館排字即工人,然則先生家應門之婢亦工人」,若發生革命,他們就應該首先「牛刀一試。」 這種互相攻擊是破壞性的:論戰的參與者大多屬於中國的精英讀書人群體,如果按照階級分析,他們不僅無法被歸入承擔革命歷史使命的階級,甚至很難避免淪為革命對象(中國此時缺乏真正意義上的資產階級的事實更凸顯了這一局面)。雖然梁啟超等人更容易被指責為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即使是中國共產黨,由於其早期幾乎由清一色的知識分子組成,它工人階級政黨的屬性也經常受到質疑,知識分子與廣大民眾的關係也很快就成為早期黨員反覆討論的一個中心問題。
總的說來,這是一場主要發生在遠離中國內地的精英知識分子內部的辯論。這種精英性以及與一般民眾的距離在論戰的另一關鍵主題——布爾什維主義是否適用於中國——上表現得更為明顯。問題的焦點在於中國能否又應否像俄國那樣發動一場暴力勞農革命並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雖然李大釗與傅斯年等人在之前就看到了俄國革命的潛力, 但只是到這個時候,它才成為了中國社會改造運動的關鍵主題——以至於張東蓀一度認為這場論戰根本就該叫做關於布爾什維主義的論戰。
這多少提示了五四后新文化運動的整體走向。此前的社會改造運動本均具有明顯的以社會刷新政治的特徵(王光祈甚至認為這就是他們與清末新派的基本不同所在),且李大釗在一年多前已提出「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的著名主張,但社會主義論戰則提示著一個相反趨向的出現,那就是政治解決重新開始上升。
與之相關的則是五四后「德先生」理想的分裂。「德先生」的最大推動者陳獨秀在論戰中對布爾什維主義式的「開明專制」作出毫不含糊的肯定, 就體現了這一點。事實上,雖然「德先生」之前被當作是屬於平民的主義,但由新派知識分子與學生加以提倡的該觀念有著內在的精英性——晚清以來對中國人民政治程度的討論在論戰中再次出現,陳獨秀等人傾向於否定人民的能力,認為必須在精英群體主導下徹底改變民性才能建立民主政治。這種強烈的啟蒙心態讓他們與中國的廣大內地拉開了距離。
大致說來,不管是出於主動的選擇還是被動的跟隨,試圖超越中國內地的現狀並直接將自己心目中「最新最好」的西方學說應用於中國的趨向程度不等地存在於論戰雙方的身上。雖然自清末以來,俄國就被認為是西方列強中與中國國情最為接近的一國(當然這裡不言明的是,它被認為是西方諸強中最落後的一國)。但此時陳獨秀等人對俄國的推重,卻是著意於其「超越舊世界」的一面;反過來,為表示回應與對抗,張東蓀等人不得不忽視英國與中國巨大的國情差異,開始主張英式的基爾特社會主義,理由則是「大凡最晚出的比較上必是最圓滿的——如基爾特社會主義最晚出的,所以他在比較上是最圓滿的。」 很明顯,他們的著意所在也是就代表「最新最好」的西方而言,誕生尚不足十年的基爾特社會主義似乎比馬克思主義更有資格。這都顯示出試圖「進入世界」的心態對論戰雙方思想與認同所具有的巨大約束力。
事實上,對這些大都居於通商口岸的新知識分子來說,論戰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到底哪一個外來主義是適合中國(尤其是內地)國情的,他們心目中的「中國」各不相同,這「複數的中國」里的每一個又都有著很大的虛懸想象的成分。雖然陳獨秀主張自上而下變革多少是退回到了清末忽視下層的「政治解決」路向,但主張社會刷新政治的王光祈等人與內地與中國國情也並不接近。考慮到論戰的思想主題選擇、論辯方式甚至是論爭結果在很大程度上都受論戰參與者社會位置、心態與認同的影響,因此,要理解這一外來主義與本國國情的爭論,就必須首先把握新知識分子與廣大內地與民眾的多層面距離,具體言之,在論戰的思想層面之外,張東蓀論戰發生前曾陪伴羅素到湖南演講(歷時不到半個月),這是論戰得以發生與展開的特定心態與認同語境,影響著各方的參與方式甚至是具體主張。以下,我們將藉助地域與認同的視野,考察這一特定事件的多方面象徵內涵及其與社會主義論戰的思想層面的複雜勾連。
2
論戰中各方的內地形象與認同
張東蓀與羅素等人的湖南之行雖然以引發社會主義論戰而被記入歷史,但記入的方式卻頗為簡略,專題性研究與通論性著作大都強調社會主義論戰爆發的必然性,因此對該事件的作用多僅僅一帶而過。
不過,除了主張資本主義,當時人對張東蓀尚有另一個共同的質疑,那就是他是否有為內地代言的資格。論戰參與者具有多重身份,他們不僅自認或被認為是共產主義者或小資產階級,也是在上海或北京的內地人,身上交織著內地與沿海、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多重矛盾,這些都在社會主義論戰中或隱或顯地起著作用。就這個層面而言,湖南之行對理解社會主義論戰則至關重要。
張東蓀的短評激起強烈回應的,是他說自己到了內地才知道住在通商口岸的人實在並不了解中國的實際情形,並以此作為自己轉而主張發展實業的理由。他此前作為上海的知名報人與政論家,是新文化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的積極參與者,甚至在1920年上半年一度參與了中共最初的組黨活動。僅因為一次內地之行就改變之前主張社會主義的立場,自然很難取信於之前與他過往頗多的陳獨秀等人。尤其是他就住在上海,這番感言卻不是自責而是指責「住在通商口岸」的「有一部分人」,這種評論姿態很容易被敏感地理解為以對內地的了解質疑對方的論辯資格。陳望道就直接質問說:「你東蓀是不是這一部份里的一個人?」 明顯是對他這種將自己排除在外的批評方式感到不滿。而內地情形到底如何也因此從一開始就成了論戰的一個主題。
初看起來,他們似乎不無道理。張東蓀之前始終活動於北京、上海與蘇州三地,都是中國最西化的地方; 他這次到內地前後不過半月,在湖南不過約一星期,如此短的時間,只夠走馬觀花(兩湖地區的方言他未必能聽懂多少,跟真正的當地人恐怕也溝通不多),很難有什麼深入認識。反過來,與出生於杭州的他不同,他的論辯對手中倒有不少出生於湖南的人——參加社會主義論戰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以湖南人為最多(較著名的就有李達、周佛海、蔡和森與李季)。 另外,兩湖本是國民黨最重要的根據地之一(黃興與宋教仁便出自這裡,辛亥革命也是在兩湖爆發)。在這種情況下,張東蓀的主張在他們聽來不啻是說他比自己要更了解家鄉與故地,這自然讓他們深感不滿。事實上,攻擊張東蓀最激烈的人,除了陳獨秀,就是李達與李季這兩個湖南人。李達在他那通篇嬉笑怒罵的《張東蓀現原形》中特地強調自己是「一個由內地初到上海的人」, 李季則處處以「我們湖南人」自命,自稱「我是湖南平江人,我住在鄉下十四年,我的親戚朋友半是鄉下人,所以我對於農民的狀況,頗知道一點,」並頗具反戈一擊意味地說他是看了張東蓀的時評,才知道「這位先生是一個市民,是不常到鄉下去的」。 兩人都以其作為湖南人的資格,刻意凸顯江南與湖南的地域差異,言下之意自然是張東蓀對內地與鄉村的了解無法與自己相比。
當然,時間長短與了解程度並不成正比關係,身在廬山中之人有時反不如山外人能看到全貌,而了解程度與能否提出要害問題更是沒有直接關係——在這一點上,今人愛說的「問題意識」倒是更關鍵的。張東蓀的評論中真正涉及內地的僅僅一句,那就是「中國真窮到極點了」。 這確是如他的批評者所說,是無人不知哪個不曉的大白話;不過,重要的是他藉此正式提出了社會主義運動是否適合於中國國情的問題;更廣而言之,在晚清以來一系列新政治與文化變革的大背景下,他實際上是在重新提出一個日益嚴重的問題,那就是新派與一般民眾的疏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