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星運 2018年天秤座8月運勢 [2018/07]
- 兒童15種常見行為背後的心理原因 [2018/07]
- 情場上擅長使用欲擒故縱法的星座 [2018/06]
- 第一星運 2018年射手座8月運勢 [2018/07]
- 十二星座7月月運 [2018/07]
- 陽曆6月喜得貴人的4大生肖 [2018/07]
- 第一星運:水瓶座2018年運勢 [2018/07]
- 第一星運 2018年雙魚座8月運勢 [2018/07]
- 第一星運 2018年水瓶座8月運勢 [2018/07]
- 第一星運 2018年天蠍座8月運勢 [2018/07]
- 警示:3種行為會折損福報 [2018/03]
- 家長要正確面對孩子間的推推搡搡 [2018/06]
- 愛情會影響事業的星座 [2018/05]
- 哪些生肖無法忍受單身? [2018/05]
- 不發脾氣能養出有規則的孩子嗎? [2018/05]
- 易患婚前恐懼症的六種女命 [2018/05]
- 男子漢要從小培養 [2018/05]
- 愛情會影響事業的星座 [2018/05]
- 對人生很實用的幾則心理學 [2018/05]
- 家長這5種行為會寵壞孩子 [2018/05]
「現在鄉村逐漸流行讀書無用論,認為寒門很難再出貴子。這樣的觀點讓我覺得挺無奈的。」何江說,「教育能夠改變一個人的生活軌跡,能夠把一個人從一個世界帶到另一個不同的世界。我希望我的成長經歷,能給那些還在路上的農村學生一點鼓勵,讓他們看到堅持的希望。」
再苦再窮也不讓兒子成為「留守兒童」
上世紀80年代的湖南農村,像當時中國所有的農村一樣,以土坯房為主,孩子的零食以糖水為主。新中國成立以後的第一代「留守兒童」就在那時誕生,越來越多的農村父母到上海、廣州等經濟發達城市打工,老人照顧幾個年幼在家的孩子。
1988年,湖南省長沙市寧鄉縣南田坪鄉停鍾村的一戶農民家中,何江呱呱墜地。與村裡其他農戶明顯不同的是,雖然家裡經濟條件一般,但何江的父母卻有個堅定的信念——不能為了打工掙錢,而讓兒子成為「留守兒童」。
幾年過去了,外出打工掙錢的人家,又是砌磚瓦房子,又是給孩子帶禮物;但是何江的家,仍是一個土坯房子。何江印象最深的,是睡前故事。無論白天農活兒幹得多累、多苦,何江的父親都會在睡前給兩個兒子講故事。
幾乎所有的故事,都是一個主題——好好學習。
「我爸高中都沒畢業,也不知道哪裡找來那麼多的中國傳統故事。每天講都講不完。」何江上大學后,有一次問起父親,哪裡找來那麼多睡前故事,父親告訴他,很多故事都是自己瞎編的,目的只是想告訴孩子,只有讀書才能有好的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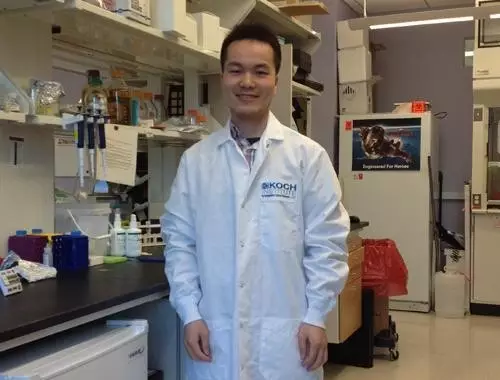
何江在美國實驗室
除了給兒子講睡前故事,何江的父親還嚴格要求兩個孩子的學習。放學后,何家的兩個兒子通常是被關在屋裡「自習」,作業做完了,繼續自習;而這個時候,大多數農村男孩都在田間地頭玩耍。
「那時覺得爸爸很『霸蠻』。但現在想想,這是農村環境下的最佳選擇。」何江後來考上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又去哈佛大學碩博連讀,而他的弟弟則成了電子科技大學的碩士畢業生,今年下半年就去上海工作了。
文化水平不高的母親懂得鼓勵孩子
支撐兩個男孩保持學習興趣的,是那個「文化水平不如爸爸」的母親。在何江眼中,母親是個溫和派。父親批評孩子學習不好時,母親總會在一陣狂風暴雨後笑呵呵地跑過來,送上「和風細雨」。
在母親那裡,兩個兒子總能找到自信。何江現在知道,母親當年的做法,就和如今他所見到的美國人的做法一樣——以鼓勵孩子的方式,給予孩子最大的自信。
湖南農村的婦女,在農閑時通常喜歡聚集在一起嘮家常。但何江的母親更喜歡陪著兩個兒子一起學習。因為不識字,她總是要求兩個兒子把課本里的故事念給自己聽,遇到聽不懂的地方,她還會跟兩個兒子討論。
何江記得,自己和弟弟都喜歡給母親「上課」。母親的循循善誘與何江如今正在接觸的美國文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我剛來美國時很不習慣,不管提什麼建議,導師都說可以試試看。」何江說,「美國有一種「鼓勵文化,無論是諾貝爾獎得主,還是那些名字被印在教科書上的「牛人」,都會習慣性地給予學生鼓勵。他們會在跟你一起啃漢堡、喝咖啡、泡酒吧時,時不時地鼓勵你一番,讓你覺得「前途不錯」。
何江在演講綵排
對一個英語是母語的學生來說,這都有極大的難度。更何況何江從小在湖南農村長大,初中才開始接觸英語,操著一口「農村英語」上了縣城的高中。那是他第一次從農村走進城裡。在寧鄉縣城,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英語水平與城裡孩子的巨大差距。「第一學期很受打擊,考試沒問題,就是開口說英語很困難」。
不怕「使苦勁」的何江,買了一本英文版的《亂世佳人》回宿舍「啃」,遇到讀到不懂的地方,就在書本旁邊進行大段大段的標註。
「學英語,跟任何一門學科的學習一樣,沒有捷徑。」 何江自認為自己有些「一根筋」。這一點,或許遺傳自父親——從來不懂得走捷徑,家裡的田地里,除了水稻,再也沒有種過其他品種的農作物。
到了哈佛大學,何江又像剛上高中那會兒,焦慮不已。中國學生大多喜歡跟中國學生聚集在一起,這樣的話,很難找到機會練習英語。
何江硬著頭皮,申請給哈佛的本科生當輔導員,「也不知道自己哪裡來的勇氣,反正就是想多講講英語」。從入學第二年開始,何江給哈佛的本科生做輔導員,這種方法讓他的英語表達方式很快從「中式」轉到了「美式」。到了讀博士期間,何江就可以給哈佛本科學生上課了。
這次申請畢業典禮演講,歷經3輪選拔才正式入選。「哈佛往屆畢業生代表大多是文科學生,我提出了一個不同的理科生視角,這可能是打動評委的關鍵原因。」何江謙虛地說。

何江在哈佛畢業典禮上演講,左邊為另一位演講嘉賓、導演斯皮爾伯格
何江演講的題目是《蜘蛛咬傷軼事》(The Spider』s Bite)。他以自己幼年時在中國農村被蜘蛛咬傷,母親用傳統土法治療的故事為引,解釋了自己的科研意義:
「作為世界不同地區的溝通者,並找出更多創造性的方法將知識傳遞給像我母親或農民這樣的群體。同時,改變世界也意味著我們的社會,作為一個整體,能夠更清醒的認識到科技知識的更加均衡的分佈,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關鍵環節,而我們也能夠一起奮鬥將此目標變成現實。」

哈佛博士畢業后,何江將赴麻省理工學院進行博士后研究。
來看看何江的哈佛大學畢業典禮演講視頻,
演講中譯文:
蜘蛛咬傷軼事
在我讀初中的時候,有一次,一隻毒蜘蛛咬傷了我的右手。我問我媽媽該怎麼處理---我媽媽並沒有帶我去看醫生,她而是決定用火療的方法治療我的傷口。
她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幾層棉花,棉花上噴撒了白酒,在我的嘴裡放了一雙筷子,然後打火點燃了棉花。熱量逐漸滲透過棉花,開始炙烤我的右手。灼燒的疼痛讓我忍不住想喊叫,可嘴裡的筷子卻讓我發不出聲來。我只能看著我的手被火燒著,一分鐘,兩分鐘,直到媽媽熄滅了火苗。
你看,我在中國的農村長大,在那個時候,我的村莊還是一個類似前工業時代的傳統村落。在我出生的時候,我的村子裡面沒有汽車,沒有電話,沒有電,甚至也沒有自來水。我們自然不能輕易的獲得先進的現代醫療資源。那個時候也沒有一個合適的醫生可以來幫我處理蜘蛛咬傷的傷口。
在座的如果有生物背景的人,你們或許已經理解到了我媽媽使用的這個簡單的治療手段的基本原理:高熱可以讓蛋白質變性,而蜘蛛的毒液也是一種蛋白質。這樣一種傳統的土方法實際上有它一定的理論依據,想來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作為哈佛大學生物化學的博士,我現在知道在我初中那個時候,已經有更好的,沒有那麼痛苦的,也沒有那麼有風險的治療方法了。於是我便忍不住會問自己,為什麼我在當時沒有能夠享用到這些更為先進的治療方法呢?
蜘蛛咬傷的事故已經過去大概十五年了。我非常高興的向在座的各位報告一下,我的手還是完好的。但是,我剛剛提到的這個問題這些年來一直停在我的腦海中,而我也時不時會因為先進科技知識在世界上不同地區的不平等分佈而困擾。現如今,我們人類已經學會怎麼進行人類基因編輯了,也研究清楚了很多個癌症發生髮展的原因。我們甚至可以利用一束光來控制我們大腦內神經元的活動。每年生物醫學的研究都會給我們帶來不一樣突破和進步---其中有不少令人振奮,也極具革命顛覆性的成果。
然而,儘管我們人類已經在科研上有了無數的建樹,在怎樣把這些最前沿的科學研究帶到世界最需要該技術的地區這件事情上,我們有時做的差強人意。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世界上大約有12%的人口每天的生活水平仍然低於2美元。營養不良每年導致三百萬兒童死亡。將近3億人口仍然受到瘧疾的干擾。在世界各地,我們經常看到似的由貧窮,疾病和自然匱乏導致的科學知識傳播的受阻。現代社會裡習以為常的那些救生常識經常在這些欠發達或不發達地區未能普及。於是,在世界上仍有很多地區,人們只能依賴於用火療這一簡單粗暴的方式來治理蜘蛛咬傷事故。
在哈佛讀書期間,我有切身體會到先進的科技知識能夠既簡單又深遠的幫助到社會上很多的人。本世紀初的時候,禽流感在亞洲多個國家肆虐。那個時候,村莊里的農民聽到禽流感就像聽到惡魔施咒一樣,對其特別的恐懼。鄉村的土醫療方法對這樣一個疾病也是束手無策。農民對於普通感冒和流感的區別並不是很清楚,他們並不懂得流感比普通感冒可能更加致命。而且,大部分人對於科學家所發現的流感病毒能夠跨不同物種傳播這一事實並不清楚。
於是,在我意識到這些知識背景,及簡單的將受感染的不同物種隔離開來以減緩疾病傳播,並決定將這些知識傳遞到我的村莊時,我的心裡第一次有了一種作為未來科學家的使命感。但這種使命感不只停在知識層面,它也是我個人道德發展的重要轉折點,我自我理解的作為國際社會一員的責任感。
哈佛的教育教會我們學生敢於擁有自己的夢想,勇於立志改變世界。在畢業典禮這樣一個特別的日子,我們在座的畢業生都會暢想我們未來的偉大征程和冒險。對我而言,我在此刻不可避免的還會想到我的家鄉。我成長的經歷教會了我作為一個科學家,積極的將我們所會的知識傳遞給那些急需這些知識的人是多麼的重要。因為利用那些我們已經擁有的科技知識,我們能夠輕而易舉的幫助我的家鄉,還有千千萬萬類似的村莊,讓他們生活的世界變成一個我們現代社會看起來習以為常的場所,而這樣一件事,是我們每一個畢業生都能夠做的,也力所能及能夠做到的。
但問題是,我們願意來做這樣的努力嗎?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我們的社會強調科學和創新。但我們社會同樣需要注意的一個重心是分配知識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改變世界並不意味著每個人都要做一個大突破。改變世界可以非常簡單。它可以簡單得變成作為世界不同地區的溝通者,並找出更多創造性的方法將知識傳遞給像我母親或農民這樣的群體。同時,改變世界也意味著我們的社會,作為一個整體,能夠更清醒的認識到科技知識的更加均衡的分佈,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關鍵環節,而我們也能夠一起奮鬥將此目標變成現實。
- [07/11]12生肖一周運程吉凶預測
- [07/12]防微杜漸!下半年或遭遇出軌風波的星座
- [07/12]為什麼兒童間學業成績有差異?因為沒上早教嗎?
- [07/14]分手后還能做朋友的血型排行
- [07/14]陽曆6月喜得貴人的4大生肖
- [07/14] 讀書改變命運 他是怎樣登上了哈佛畢業典禮的演講
- [07/17]熊孩子,只能贏不能輸
- [07/17]先好好愛自己孩子,再創業拯救別人孩子
- [07/17]十二星座7月月運
- [07/18]大衛談占星?|?原來12星座眼裡成功的區別這麼大
- [07/18]哪些雷區你一碰,老公就翻臉
- [07/18]12星座可以嘗試的15件小事丨雙子月還能這麼玩!
- [07/23]第一星運:12星座2018年運勢
- 查看:[夏威夷之戀的.最新博文]
- 查看:[大家的.最新博文]
- 查看:[大家的.娛樂八卦]
評論 (0 個評論)
- mali50:六月的秋褲
- 8288:《戰狼Ⅱ》成了奧斯卡最大的笑料
- 農家苦:人老是從屁股開始的
- 前兆:小神童的特殊技能
- 量子在:賈乃亮的往日讚美歌
- YHOO:錢能讓人心情鬱悶,決定把錢扔掉
- 8288:每個優雅的老人心裡,都住著一顆不老的心
- 量子在:有些爭議的一齣戲
- 金角大王:論壕紳郭先生之十大「功德」(一)
- 楊立勇:蔡氏工作室的菜譜
- 遊子彗星:林志玲遭郭文貴亂爆 晚間12字怒斥謠言!
- 楊立勇:讀書筆記:《人微言不輕》(Crappy Little Nobody) 作者:安娜.肯德里克(Anna Kend
- 農家苦:為什麼不裝贔?
- YHOO:寵物蛇困在耳洞
- 往事並不如煙:春晚小品
- Nanshanke:棋聖乎?棋渣乎?
- kylelong:當代流行「腿咚」?
- YHOO:馬來西亞的環球小姐服裝吸引了各種各樣的反應
- jc0473:能伸能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