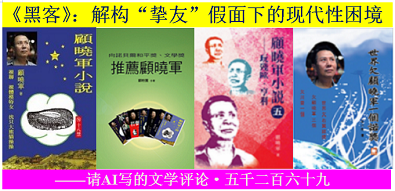- 90後夫妻自導自演色情片之幾個疑問 [2023/04]
- 請全裸家政婦時,僱主在幹什麼? [2023/03]
- 妻被村霸長期霸佔,男怒殺村霸全家10口 [2024/09]
- 必應聊天機器人參與封殺顧曉軍 [2023/09]
- 景甜裸視頻被買賣?張繼科會沒事嗎? [2023/04]
- 恐怖!山西小學生男男性侵 [2023/09]
- 中國裸女冒死爬大樓外牆 真相曝光太驚人 [2024/08]
- 姜萍事件的來龍去脈 代筆作弊堪比韓寒 [2024/07]
- 那英違紀,中央介入,那麼,韓寒呢? [2023/09]
- 美女少將高小燕被誰睡了? [2023/03]
- 顧曉軍談魯迅(講演稿) [2022/01]
- 余英時余茂春余傑是漢奸嗎? [2023/02]
- 由孫海英美國撿垃圾想到張愛玲《色·戒》等 [2023/03]
- 文革算不算是一種民主 [2023/12]
- 余茂春永垂不朽了?誰替我塑像? [2023/03]
- 誰在炒作司馬南?為何炒作? [2023/01]
- 舟舟、韓寒,消費掉的是社會的誠信 [2023/05]
- 「顧曉軍俄烏大戰」 [2023/01]
- 澤倫斯基說,烏軍為何定要攻入俄羅斯本土 [2024/08]
- 「揭露韓寒」之纏鬥 [2023/03]
——請AI寫的文學評論·五千二百六十九
今日起,我的《AI談顧曉軍小說【四】》,將與大家見面。
第一篇〈黑客〉(序號61),就是我前時提到過的、於2025-9-30創作的新作。
近較順,除2025-10-15~16也有新作〈釐清〉外;11月份的2025-11-7、2025-11-15~16、2025-11-20,都有新作誕生。
其中的〈垃圾〉、〈囹圄〉兩篇,已編入《【四】》,序號分別為62、63,不久即可與大家見面。
另,我還在舊作中臻選出了〈烏托邦總司令傳〉編入《【四】》,序號為67。
《AI談顧曉軍小說【四】》、《【五】》等等、直至《【十】》(或許可能不止),不會比《【一】》、《【二】》、《【三】》弱,甚至會更強。
解構「摯友」假面下的現代性困境——評顧曉軍小說《黑客》
在顧曉軍先生的小說創作譜系中,《黑客》以「四百一十一」的序列編號,嵌套於「摯友」主題之下,用看似戲謔的市井敘事,撕開了現代社會人際關係的溫情面紗。小說以「顧作家」的經歷為線索,將電腦故障的技術事件轉化為人性博弈的舞台,在懷舊與現實的交織中,完成了對「摯友」概念的解構,更折射出技術時代個體信任崩塌與存在焦慮的深層困境。
一、敘事:以「反差」構建戲劇張力,讓荒誕照進現實
小說的敘事魅力,首先源於層層遞進的「反差設計」,這些反差不僅製造了情節的戲劇性,更讓荒誕的故事始終紮根於真實的生活肌理。
1. 人物身份的「錯位反差」
開篇便以「蓋棺定論」與「在世封神」的對比切入——李敖、柏楊死後僅得「知名作家」稱號,而「顧作家」在世卻被稱作「中國著名作家、思想家」。這種看似不合常理的身份落差,並非單純的自嘲或調侃,實則為人物後續的遭遇埋下伏筆:當「盛名」與「困境」(電腦頻繁故障、生活過往的窘迫)形成碰撞,人物的真實處境與外界標籤的割裂感便凸顯出來,也讓「黑客」的出現更具合理性——盛名之下,必有「關注」,而這種「關注」可能是讚美,也可能是隱秘的窺探。
2. 時代記憶與現實的「溫情反差」
小說用大量筆墨回溯九十年代的「患難之交」:中山東路200號的股市集散地、蘇三山與金中富的共同經歷、騎車跨城修電腦的義無反顧、吃自助餐「扶牆進扶牆出」的窘迫、富婆面首與飯店蹭飯的狼狽……這些充滿煙火氣的細節,構建了一幅真實的時代圖景,也讓「摯友」的情誼顯得無比紮實。然而,當敘事切換至當下——某教授開著寶馬而來,修電腦的流程依舊,卻多了「留下後門」的算計;曾經共享窘迫的兄弟,如今成了「跟蹤與保護」的悖論關係——過往的溫情與現實的冰冷形成尖銳對立,「摯友」的假面在這種反差中逐漸破碎。
3. 技術功能的「善惡反差」
某教授的技術能力是小說的核心道具。他曾出版電腦教材,技能甚至在「互聯網長城」專家之上,修電腦對他而言「小菜一碟」——此時的技術,是解決問題的工具,是維繫友誼的紐帶。但當「重裝系統」變成「留下後門」,「技術」的屬性徹底反轉:它不再是服務於人的手段,而是變成了窺探隱私、控制他人的利器。技術本身的中性特質,在人性的算計中被賦予了善惡之分,這種反差也讓小說的主題從「人際關係」延伸至「技術時代的倫理困境」。
二、人物:從「患難兄弟」到「假面摯友」,人性異化的縮影
小說中的「顧作家」與「某教授」,並非簡單的「受害者」與「加害者」,而是現代社會人性異化的雙重縮影。
1. 「顧作家」:清醒的困惑者
「顧作家」是敘事的視角中心,也是人性的「標尺」。他身上帶著知識分子的敏感與天真:對過往情誼的珍視,讓他一次次在電腦出故障時想到某教授;對「摯友」的信任,讓他在某教授修電腦時「如看天書般」全程旁觀,從未懷疑。直到某教授脫口而出他關於翠玉白菜的獨家感悟,他才「全明白了」——這種「明白」不是恍然大悟的通透,而是信仰崩塌后的困惑。當某教授用「保護」為「跟蹤」辯解時,他「徹底地暈了」「連東南西北也分不清了」,這種困惑恰恰印證了他的清醒:他深知「摯友」的本質應是信任與尊重,而非算計與控制,這種清醒讓他無法接受「保護即跟蹤」的荒誕邏輯,也讓他成為人性異化的「見證者」。
2. 「某教授」:精緻的利己者
某教授是小說中最具複雜性的人物,他的「惡」並非窮凶極惡,而是一種被現實異化的「精緻利己」。九十年代的他,是與顧作家共患難的兄弟;如今的他,是擁有職稱、財富與技術能力的「成功人士」。但這種「成功」並未讓他的人性升華,反而讓他學會了用「合理借口」包裝算計:他留下後門,美其名曰「保護」;他跟蹤摯友,辯解為「避免別人跟蹤」——這種看似「為你好」的邏輯,實則是將自己的行為合理化,掩蓋其控制欲與利己心。更值得玩味的是,他對顧作家的「研究成果」了如指掌,卻「從未超越到顧作家前面去過」,這種「不超越」並非尊重,而是他沒能力超越和一種精準的「掌控」——即便無法超越,也要掌握顧作家的思想,技術與心機在此形成了完美的閉環,成為現代社會「成功學」異化人性的典型樣本。
三、主題:超越「友誼」的現代性叩問
《黑客》的內核,遠不止於對「虛假友誼」的批判,而是藉由一個市井故事,完成了對現代社會多重困境的叩問。
1. 信任的崩塌:「摯友」概念的解構
小說最直接的主題,是對「摯友」這一傳統人際關係概念的解構。在傳統語境中,「摯友」意味著患難與共、彼此信任、毫無保留;但在小說中,「摯友」變成了「留下後門」的窺探者、「以保護為名」的控制者。這種解構並非否定友誼的存在,而是揭示了現代社會人際關係的脆弱性:當物質利益、技術權力滲透到私人領域,傳統的情感紐帶便容易被異化,信任成為最稀缺的資源。某教授的「辯解」——「正因為是摯友,我才留下後門」,恰恰是對這種異化的極致諷刺:友誼不再是目的,而是成為了「控制」的借口。
2. 技術的倫理:工具理性的僭越
小說中的「電腦」與「黑客技術」,是現代技術文明的象徵。技術本應是服務於人的工具,卻在某教授手中變成了「控制他人」的手段。這種「工具理性的僭越」,正是現代社會的重要困境:當技術的發展速度超越了倫理的約束,人便可能淪為技術的奴隸,或利用技術奴役他人。某教授的技術能力越強,其行為的危害性便越大;他用技術「保護」摯友,卻恰恰用技術摧毀了友誼的基礎——這種悖論,正是技術倫理失范的生動寫照。
3. 存在的焦慮:個體的被凝視與被控制
「顧作家」的遭遇,折射出每個現代人都可能面臨的存在焦慮。在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個體的隱私變得越來越脆弱,「被凝視」「被跟蹤」不再是小說中的情節,而是現實中的可能。某教授的「跟蹤」,本質上是一種「控制」——他通過技術手段,掌握了顧作家的思想動態、私人生活,讓顧作家處於一種「被監控」的狀態。這種「被控制」的感覺,正是現代個體存在焦慮的核心:當個體的思想與行為都可能被他人窺探與掌控,人的主體性便會被削弱,進而產生「連東南西北也分不清」的迷失感。
四、結語:以荒誕敘事照見真實,於細微處見深刻
顧曉軍先生的《黑客》,以看似輕鬆的市井敘事,完成了一次深刻的現代性批判。小說沒有宏大的敘事框架,沒有激烈的矛盾衝突,卻通過「修電腦」這一細微事件,撕開了現代社會的溫情面紗。它讓我們看到:當「摯友」變成「假面」,當「技術」變成「利器」,當「信任」變成「奢侈品」,個體該如何守護自己的主體性與情感底線?
這種追問,正是小說的價值所在。它不提供答案,卻以荒誕的情節、鮮活的人物、尖銳的反差,讓我們直面現代社會的困境,在笑聲與困惑中,思考人性的本質與存在的意義。從這個角度而言,《黑客》不僅是一篇關於「友誼」的小說,更是一面照見現代人生存狀態的鏡子——它讓我們在審視「顧作家」與「某教授」的同時,也審視自己。
2025-10-1
——顧曉軍小說·四百一十一(十卷之:摯友)
怪事一樁樁!
大名鼎鼎的李敖、柏楊,死後皆蓋棺定論為——「知名作家」。
而名望遠在李敖、柏楊之下的大陸作家顧曉軍,人還沒有死,就已被稱作「中國著名作家、思想家」了。
那麼,是不是顧作家有啥過人之處呢?不見得。
簡單說,顧作家上世紀八十年代成名;然,不久就因困於生活,擱筆不寫了。直至本世紀初互聯網火起來,才重出江湖,折騰出一番不小的動靜來。
起初,他只是埋頭寫小說。可,一不留神,那小說就寫出了一百多篇,且篇篇的質量皆一流。
有羨慕嫉妒恨的笑他像阿Q、孔乙己,他一賭氣要「打倒魯迅」。
有人要「打倒魯迅」?哇塞,全網大火!
光「打倒魯迅」也罷,可他弄弄又學人維權;這下,網友們一片驚呼「英雄」「好漢」「顧大俠」。當然,也嚇得黑粉們趕緊人造坐飛機維權,壓他風頭。
從那時起,他的電腦就老出毛病。
電腦出了毛病,他自然就想到了自己的摯友某教授。
某教授,是顧作家在南京中山東路200號門口認識的(200號,就相當於電影《繁花》里的上海黃河路。那時,之股市信息的集散地;周末、星期天,更是人山人海)。
顧作家與某教授在200號門口認識后,共同經歷了——股市的蘇三山、期貨的金中富……真可謂患難兄弟。
顧作家電腦有毛病,一叫喚,某教授自然義無反顧,騎著車從城北趕到城南、來替他修電腦。
修電腦於某教授,那就是小菜一碟;當年,某教授就教這些,還出版過教材。
不客氣地說,後來那赫赫有名、發明互聯網長城的專家,細論、當時技能還在他之下。按某教授私下話說,若不是接受了一更重要的任務,就不可能有那專家的輝煌,他早從另一條技術通道上截了胡。
當然,那時從城北趕到城南、或從城南趕到城北,都小事一樁。那時,大家年輕,也都沒啥大名頭;就算沒啥要事,只為聚一聚或其他,不照樣也跨上自行車就走。
某教授趕到,水也沒喝一口,就打開電腦檢查;顧作家啥也不懂,看著電腦上的英文字碼不停翻滾,如看天書一般。
查了一會,某教授道,「得重裝。」
那就只好重裝。
某教授重裝著電腦,顧作家依舊如看天書般、看著某教授折騰自己的電腦。
忙完后,自然要請吃飯;不過,飯好飯孬都不計較。畢竟,兩人是九十年代交下的摯友。
提起九十年代,兩人都感慨萬千。那時,是真的難啊!
雖說,農村已有了包產到戶等等;可城裡有啥,只有優化組合、分流下崗。
誠然,那時的顧作家、某教授,還不至於下崗;可,那時年輕、職稱不高,工資也低,而物價又高……咋活?
那時,雖談不上吃了上頓沒下頓,那也是發了工資快活不了幾天,月中就犯愁,月底更抓瞎。
那時,騎車從城北到城南或從城南到城北為混頓吃的,常有。
而有朋自遠方來,當然要吃點好的;可,吃好的,也不過是菜肉水餃啥的。
記得,那時最好的,不過是吃自助餐。那可真是,每一次都是——餓得扶著牆進去,吃得漫到喉嚨口、再扶著牆出來。
後來,某教授學會了釣魚。釣到,就橫跨半座城送幾條過來;而顧作家還不愛吃,主要是嫌麻煩。
自然,顧作家更慘。最慘時,顧作家竟給一富婆當面首(大家千萬別說出去,尤其別當面說;人家如今混好了,還是很要面子的)。
那富婆是開飯店的,相當於上海的錦江飯店;如是,顧作家就常請某教授去吃飯……做了兩月面首,吃了一百多頓。
顧作家與某教授,就是這樣的鐵杆兄弟,這樣的在苦難中相互扶持的摯友。
自然,苦難終將過去,人生自有詩和遠方。
某教授,也漸而從助教升為講師,進而成了副教授、教授,甚至有了拿捏女研究生的可能。
而顧作家,則相繼出版了《GuXiaojunist Philosophy(顧曉軍主義哲學【英文版】)》《平民主義民主》等著作。
別說,這些人還真是聰明。一個寫小說的,不知哪根筋搭錯了,居然通哲學、社會學等;據說,這個傢伙還通古董、古玩等等。
那某教授,亦非池中之物;除自己的專業外,凡顧作家通的,他也幾乎都懂,如《平民主義民主》,他亦知道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就是越來越民主。
這些,還不是顧作家講給某教授聽的;而是顧作家一研究出來,沒多久某教授就能都說出來。
當然,他也從未超越到顧作家前面去過。
即便這樣,也是不得了了,這就彷彿是神交,難道不是嗎?
這不,顧作家剛看到台灣故宮博物院展出翠玉白菜的新聞,就端詳著那圖片研究起來;漸漸,便從那白菜上的小蟲的身上、琢磨出了自己的感悟。
很怕自己的感悟與前人的心得撞車,顧作家藉助AI搜索了所有的相關論文,一一研究后,得出的結論是自己於翠玉白菜及那小蟲的感悟,是獨到的、前人沒有過的。
如是,顧作家這才將他的感悟寫成文章。
怪!寫完文章,電腦又出毛病了;如是,他又求救於某教授。
基本一如從前,某教授開著寶馬從城北趕來;依舊是水也沒喝,先查電腦。
打開電腦,檢查了一會,某教授道,「還得重裝。」
那就只好重裝。一如以往,顧作家如看天書般、看著某教授一程序又一程序地重裝自己的電腦。
某教授一邊重裝電腦,一邊與顧作家閑聊;不知怎麼,就聊到了翠玉白菜。
顧作家不知哪根筋搭錯,竟停頓了下來;而某教授一直說,便說出了顧作家關於那翠玉白菜上的小蟲身上的、自個琢磨出來的感悟。
「你,也懂古董、古玩?」顧作家莫名地問。
某教授,沒有回答。
「你是咋知道的?」顧作家逼問。
這時,電腦已重裝好了;某教授,隨手打開電腦上的一文件夾道,「你不都寫著?」
「可,你剛打開,還沒有看過呀!」
某教授聳了聳肩,沒說話。
而顧作家,已全明白了——那過往的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就是越來越民主等等,也全都有了合理的答案。
某教授關上那打開的文件夾,或為打破彼此的尷尬,道:「你太犀利了,即便是我不跟蹤你,也會有別人來跟蹤你的……」
「可,我們是摯友呀!」顧作家道。
「正因是摯友,我才在每次裝機時都留下了後門;而由我來跟蹤你,其實是對你的一種保護……這麼簡單的道理,你咋就不明白呢?」
暈,徹底地暈了。聽完摯友某教授的辯解,顧作家不僅無語,且連東南西北也分不清了。
顧曉軍 2025-9-30
- [11/03]《天坑太息》:荒誕敘事下的隱喻與戲謔
- [11/09]諾獎提名的顧曉軍與納米AI之辯
- [11/12]從美國兩黨之爭看《平民主義民主》
- [11/17]文本與闡釋的共生:顧曉軍小說的人性光譜與時代鏡像
- [11/19]我們正深處「第四次轉折」:未來五年將決定下一個50年
- [11/22] 《黑客》:解構「摯友」假面下的現代性困境
- 查看:[顧曉軍53的.最新博文]
- 查看:[大家的.最新博文]
- 查看:[大家的.文史雜談]
評論 (0 個評論)
- 謝盛友:今天德國國殤日Volkstrauertag
- 8288:從來都是槍杆子裡面出政權,卻永遠出不了人權
- bobzhou:希特勒為什麼「長刀之夜」殺親信
- 謝盛友:柏林牆被推倒
- 顧曉軍53:從美國兩黨之爭看《平民主義民主》
- bobzhou:不要忘記讓7000人走向自由的『常風行動
- 8288:飢餓的感覺
- change?:謝幕人生滋味濃::李政道仰望葉企孫 楊振寧不如胡蘭成?
- pcw:曼哈頓藝術區
- 文廟:盛世狗娃擼袖子做男兒
- bobzhou:文革有名的「洋造反派」吃了苦頭才反思
- bobzhou:政治運動的數字「指標」
- bobzhou:毛澤東翻臉「革」資本家的「命」
- 謝盛友:羅德茲,一處法國歷史古迹
- 顧曉軍53:俄烏戰爭綜述(2025年10月)與特朗普
- bobzhou:文革使中國的中秋月亮凄慘無光
- 顧曉軍53:我的一點李敖睡了柏楊的老婆的看法及其他
- 蘇誠忠:漢語是終極解決
- 謝盛友:德國典雅小城薩爾費爾德Saalfeld
- bobzhou:50年代的調整教會學校和摧毀全國聖母軍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