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南課本中的中越戰爭:中國在越南三光政策真相 [2018/11]
- 回看馬航MH370事故,60多位晶元專家喪生,誰才是真正的兇手? [2019/06]
- 在美德堡工作的印裔曝光:病毒製造后泄露,導師及知情者被暗殺 [2020/08]
- 網傳王立軍交待的部分材料流出 [2019/06]
- 間諜金無怠到底被誰出賣? [2018/12]
- 老兵披露越南女兵色誘細節 [2019/12]
- 擊斃越軍頭號美女特工阮文慧。, [2018/11]
- 毛澤東發動文革真相:並非晚年昏聵 [2018/11]
- 五名中國女子移民以色列,都因為一個虛構的猶太民族 [2019/02]
- 死亡陷阱——真實的鐵列克提事件 [2018/11]
- 一篇文章,講清楚長津湖的來龍去脈 [2021/10]
- 「餓死三千萬」原來是蔣經國出資100萬美元炮製而成的 [2019/07]
- 毛主席為何鍾情湖北?偏愛東湖? [2020/09]
- 陳永貴追悼會:八寶山冷冷清清,大寨人山人海 [2023/03]
- 關於紅衛兵運動的歷史考察 [2022/01]
- 「美國文化革命」?拜你所賜! [2020/06]
- 評謝盛友的 「鄧小平 三落三起」 [2022/12]
- 魏巍:論毛澤東晚年 [2024/11]
- 給「台獨」死硬分子拉清單意味著什麼? [2021/11]
- 永不消逝的紅色——紀念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逝世48周年 [2024/09]
「對稱」的敘事
恰如許多觀眾所提及的,公映版本的《城市夢》所試圖呈現的,是武漢城管的工作之難和攤販王老漢的生活之難之間的張力。從製作過程到公映剪輯,導演都力圖在形式上維持均衡。為了讓觀眾能夠看到不同視角的畫面,導演甚至直接組建了兩個獨立的攝製組,分別跟拍攤販和城管的視角。
可是電影真的達到了平衡的效果嗎?
王老漢一家來自河南農村,在武漢一處鬧市區人行道擺了十幾年的水果雜物攤來維持生計。在「城市發展」的主旋律下,城管局誓要將這個攤位作為攻堅戰取締。此乃背景。
在一次又一次的博弈中:城管開罰單,老漢撕罰單;城管量面積,老漢扯掉皮尺;城管記錄小攤流水,老漢窮追猛打……一個經典的鏡頭是,老漢扑打著城管中隊長的胸脯,質問:「你良心何在?」可是鏡頭一轉,城管隊長對路人淡淡地說,「年輕人扛打,只要能解決問題,挨點打不算什麼。」

拍打良心//
於是,老漢的「抗爭戲碼」被降格為發泄情緒的胡鬧。儘管畫幅嚴格遵循1:1分開,觀眾的心中卻難免浮現出「我窮我有理」的刁民老漢和忍辱負重的城管隊長的對偶。
城管隊去調查老漢的流水與利潤,進行依法取證和依法處罰,給予超出法定要求的寬限期,自掏腰包重新安置攤棚等,而老漢的態度是始終如一的油鹽不進。觀眾在這個過程中難免感到疲憊。城管的文明、忍讓和老漢的胡攪蠻纏、強詞奪理構成了鮮明的對比,難道老漢不是攫取「暴利」還裝貧賣弱嗎,難道不是老漢違法在先嗎,難道老漢不是得了便宜還賣乖嗎?
倘若僅僅在形式上平分老漢和城管的視角,觀眾很自然的就會產生這樣的想法。
當老漢——頗為令人意外地——願意放棄攤位,讓兒子得以接受城管的「善意」,挪到大學附近的新攤位;讓妻子得以在塑鋼廠門口露出了感動的表情;讓城管局長在隊長面前一本正經的口白「我們要的不是感動,而是他們自發的配合管理。」也只有在老漢無理的前提下,這個結局才會顯得「大團圓」起來。
但老漢是否無理,取決於我們從什麼角度來理解老漢的行為。
生存,本無需同情
王老漢本人患有腦梗,妻子患癌,兒子年輕時因工傷斷手,孫女在武漢讀書。這些元素在電影中反覆出現,構成了觀眾對老漢一家同情的起點。同情,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情感,它需要對象處於一種絕對的低位,一旦這個低位被動搖——觀眾發現老漢一家原來沒那麼慘或者沒那麼卑微——譬如老漢在攝像機前肆意拍打城管或者一個月流水好幾萬,這種同情就會被動搖,就會迅速的倒向另一個弱者,所謂的「工作中的弱者」。
仔細想想,這種同情的比拼毫無意義,這取決於誰掌握了話語權。以城管指控老漢「暴利」為例,城管統計暴利的方法,是用老漢最高的單日營業額扣去從網上查來的批發成本。從商業角度考慮,這忽略了老漢長期經營和籠絡客戶的投入。才獲得了「最多一天三千元」的流水。所以「營業額」的計算方法本身就不合理了。
另一方面,從「成本」角度,這個計算方法完全忽略了老漢個人生活的開銷。作為農村進城人員,老漢擺地攤雖然不納稅,但也無法享受城市醫保等社會福利,老漢一家一個月吃藥的成本就要小一萬塊錢,這筆錢卻沒被城管納入計算。倘若真的按照稅收原則收取,還不知道是老漢該給政府錢,還是政府該給老漢錢。

老漢不需要同情,求生存者當相互尊重//
但我想,我們應該從另外一個視角來理解這些元素。老漢並不是一個弱者。老漢的訴求從來不是向政府或者社會乞討福利,相反,他始終要求的是「自力更生」的權利。一系列不利的外部因素,更適合說成老漢在求生存時所面臨的困難(和作為求生存者的我們一樣)。這些客觀條件決定了在當下他生存的最佳策略是在鬧市區擺攤。
城管局長在做指示的時候,說「老漢的孫女已經是武漢人」,要「啟發他們用市民的眼光思考問題:擺攤不是長久之計。」
是的,不融入城市秩序的地攤經濟,不僅給城管工作帶來了麻煩,更無助於城市資本主義經濟的再生產。唯有變成無產階級——進工廠,才是「城市人」的長久之計。只是,尊敬的局長大人喲,老漢一家殘疾,他們不是不想成為無產階級,而是欲成為無產階級而不得(且不說兒子的手還恰恰是為資本主義砍去的)。

王老漢的兒子年輕時在台資工廠受了工傷,僅拿到社保補償兩萬元//
在生存方式這個話題上,我們不妨退一步想一想:老漢和老伴七十多歲,百病纏身,本應在養老的年紀,卻依舊起早貪黑地工作;老漢的兒子,二十歲出頭就在台資工廠把手切斷了,黑心工廠卻一分錢都不補償;老漢的孫女,出生幾個月就到了武漢,卻只有依靠和城管「不打不成交」的關係才能在此地讀書……
這些現象,已經多少讓人困惑,鏡頭描繪的是21世紀的武漢,還是19世紀的曼徹斯特?然而老漢的全部期待,仍然只是得一方水土自力更生,這是中國人民身上怎樣的忍耐精神……
可是,即便是這最低程度的期待,也要遭到一個莫名其妙的阻力。
纖塵不染的城市夢
電影中城管的策略可以簡要的分成三個條線:第一,確定老漢的流水和利潤,從而得出「老漢的經營屬於暴利」的判斷,為驅逐作道德鋪墊;第二,在法律顧問的建議下,進行取證和開處罰單,取得法律授權,劃出最糟糕的結果(暴力拆除,零補償);第三,打一巴掌給個甜棗,主動邀請老漢兒子談判,提出合作的好處——一個比「執法必嚴」要好的多的結果,最終「改造」了老漢的兒子,實現了「自覺配合管理」(城管語)。
但這三條線所編織成的「文明執法」,真的「文明」嗎?我們需要深思法律機器在城管執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通過將不平等合理化並隱藏在龐雜的法律機器之下,城管為自己的驅逐行動創造了正當性。
有人或許會指責:老漢不尊重法律,他對執法行為不贊同,可以依據(城管主動聲明的)投訴或訴訟等體制內方式來解決問題,而非抗拒執法、撕毀罰單、企圖「按鬧分配」。
可是,在影片中,城管隊員在處置老漢的「違法行為」時,尚且三番兩次的向法律顧問請教——說明與此相關的法律問題十分複雜。那麼面對這麼複雜的問題,老漢可以向哪位法律顧問求教呢?老漢又哪裡來的時間去求教呢?
除此之外,在這裡還需要提出一個更核心的問題:如果我們放棄一切既定法都是合理的先在判斷,那麼我們就不得不面對老漢的反抗所提出最根本的一個問題:人的生存與尊嚴是否高於律法?
城管在電影中三番五次的強調:「城市要發展!」略而不談的是:城市要發展成什麼樣子。答案不難設想:一塵不染的路面,寬敞的人行道,整齊劃一的門面房,有戶籍和「固定工作」的有房市民,資本一擲千金建起整齊劃一的大企業大工廠等等。在這張乾淨的圖景里,沒有販夫走卒存在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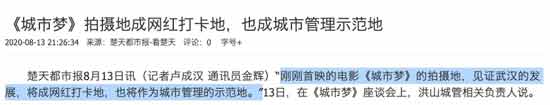
他們的「城市夢」//
中國城市的人行道時常格外的寬,甚至可以用作停車場。在其最初的構想中,這樣的人行道大概只能維持寬敞、漂亮但空曠的城市街景,但在無意之間,它為進城務工人員落腳和緩衝的地攤經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這種地攤經濟讓更多人得以在城市生存下來。像老漢兒子這樣的殘疾人,在農村或者工廠意味著喪失全部勞動能力,恐怕只能依靠微薄救濟苟延,但是寬敞的人行道卻在不經意間為他們提供了生存下去的機會——這是老漢和所有進城務工人員的「城市夢」,城管「城市夢」的對立面。
城市可以容納比農村更多樣的產業類型,可以支撐更高效的經濟活動,可以吸納高密度的人口——它可以允許更多人有尊嚴的生存,因而城市化成為了人類發展的一個階段。但能否實現更有尊嚴的生存,仍然取決於我們在城市與人之間做的排序題。城市的秩序究竟應該服務於人的生存與發展——也就是一個個「王老漢」的生存與發展,還是凌駕於他們?


格外寬敞的人行道和無法回去的故屋//
我只知道,現實的城市史,是「王老漢」不斷的湧入與城市不斷的驅離,交織著血、淚、汗的詩篇。歸去來兮,歸向何方?農村老家是一間沒辦法回頭的破屋。
正值武漢爭創文明城市前夕,紀錄片如實記錄了政府工作人員在路邊擺攤,教人背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畫面。小朋友流利洪亮的背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而另一邊,城市的起重機正將另一些人的「城市夢」拆除。這是一幅過於文明的畫面。
獅子與羚羊
強制拆除通告已經貼出,城管的策略進入了第三階段。影片後半段著力刻畫的「暖心之舉」、「人性化解決方案」,究竟暖了誰的心?僅因沒有得到權力的批准,老漢被迫放棄一半的生意(城管只承諾幫助老漢的兒子易地開水果攤,而「建議」老漢退休——自然,「退休金」自理),搬到更為冷清的大學城(重建客源要花多久的時間呢)。而當局所付出的,是一個塑鋼棚子。何其便宜的買賣!如此,他們還自認為施恩於老漢,還要沾沾自喜的拍合影,做宣傳。
面對這樣的結局,老漢的老伴和兒子卻流露出慶幸。原因何在?一方面,不可排除權力意識形態的影響;另一方面,他們是以一己之力與整個法律機器和政府力量作對抗,電影的結局,畢竟已經比很多更糟糕的結果強多了。(更不要說,幸運的被紀錄片導演選中后,攝像機鏡頭起到的客觀監督作用。)不妨看看電影中無意記錄更多擺攤人的命運:在不同地方打游擊 –> 被敲骨吸髓 –> 被趕出城市。
也只有在這個背景下,我們能夠理解老漢選擇反抗的決絕和勇敢。對於老漢來說,他難道意識不到在城管所代表的國家機器面前,自己的命運如同草芥?然而憑著一身的「抓馬」和堅定的鬥志,老漢硬是成為了城管面前一顆咽不下去的硬釘子,在鬧市區堅持了十幾年。儘管最終敗北,儘管「一手打一手談」淪為「兩手輸」,這樣的鬥志,這樣的精神,我們怎能不感到敬佩又慚愧?
誠然,我們看到老漢時而「撒潑耍賴、無理取鬧」。然而莫忘記:獅子或許可以在羚羊面前從容自得,羚羊必須在獅子面前拼盡全力。因為獅子失手一次,無非餓一頓肚子,羚羊失手一次,失去的卻是全部生命。「工作上的弱者」脫下一身藍衣,依舊可以回家享受天倫之樂;「生活上的弱者」一旦輸了一著,便必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工作上的弱者」有強大的法律機器和官僚組織作後盾,「生活上的弱者」除卻身邊的一個老太太和兒子三口人,便別無幫手。

羚羊之怒//
如果我們在接受電影信息的同時主動的關注它避重就輕的之處,我們就能意識到這個故事並沒有一個「團圓」的結局。倘若我們主動的填補回被忽略的視角,我們會看到「生活的弱者」和「工作的弱者」(城管語)之間的博弈,並不是一場平等的對戰。試圖去「平等」表現他們的人,先天的站在了強權的一邊。老漢所面對的,是一個個體絕難匹敵的龐然大物。在這個前提下,仍然堅持做一個戰風車的堂吉訶德,支撐他的不僅是生存的意志,還有反抗的決心。
正如許多武漢當地觀眾的短評都已經指出的那樣,在鏡頭面前,這部電影已經挑選出城管最文明最光鮮的一面進行表現,沒有暴力執法,沒有非法執行。一切都嚴格的按照(他們所能想象的)「文明」的最高標,一切卻不可避免的走向殘酷的最無情。
電影以「武漢被評為文明城市」與幾張王老漢與城管的近照作結,變成了照片的王老漢成為了城管宣傳的一味佐料。羚羊與獅子的搏鬥尚未結束。但能寫在電影片尾的協拍方,也只有獅子的一方。
- [09/11]戰爭一步之遙?印度正加緊向邊境增兵!
- [09/13]司徒雷登——台獨運動的一個重要推手
- [09/14]雨水與淚水交織:寶雞紀念毛主席逝世44周年,感天動地!
- [09/15]談談袁先生的外交高論
- [09/17]美國:我們一直在收買中國文人
- [09/17] 城市夢,誰的夢?
- [09/20]美國大選前瞻,及特朗普萬一連任的展望!
- [09/21]細品胡錫進同志的「國家戰略」
- [09/22]關注!美輝瑞新冠疫苗接連曝出副作用,安全第一!
- [09/23]毛主席為何鍾情湖北?偏愛東湖?
- [09/26]解除對華為禁令並非好事
- [09/28]文章內容 台灣將向何處去?台灣會獨立嗎?
- [09/29]城市裡剩女為什麼越來越多?農村的光棍也在也越來越多
- 查看:[successful的.最新博文]
- 查看:[大家的.最新博文]
- 查看:[大家的.網路文摘]
發表評論 評論 (3 個評論)

- 回復 successful
- 生存,本無需同情.

- 回復 successful
- 城管----- 就是毛澤東在建立政權以後以及在文革中,反覆批判的取締的 叫*雜鴨雜;所以在毛澤東執政期間, 是沒有這種 機構和組織的.

- 回復 successful
- 城管局長在做指示的時候,說「老漢的孫女已經是武漢人」,要「啟發他們用市民的眼光思考問題:擺攤不是長久之計。」
- light12:蘆笛 周恩來為什麼怕毛澤東?
- light12:洛拉:我家的奴隸 ---阿列克斯·提臧
- light12:蘆笛 治國白痴毛澤東:外交篇
- light12:蘆笛 治國白痴毛澤東:內政篇(一)......(八)
- light12:蘆笛舊文談中美製度比較,民主弊端,「No representation without taxation」
- light12:毛澤東的知識、智力與性格缺陷
- light12:蘆笛談64
- light12:蘆笛談64不是民主運動
- light12:蘆笛 淺探六四與其他歷史事件的相似性
- light12:任劍濤:國家理念與政府政策的大眾認可
- light12:蘆笛 試著用照片喚醒裝睡的人——致胡平兄
- qxw66:海灣以色列協議:國王沒有衣服(慶祝殘酷的獨裁統治)
- light12:劉剛 閆麗夢夥同郭文貴造假學術論文,指控武漢P4實驗室人工合成了COVID-19
- qxw66:不斬首十萬,甚至四十萬不會消停
- 8288:一部手機失竊而揭露的竊取個人信息實現資金盜取的黑色產業鏈
- light12:美國643萬!BLM越燒越猛,華埠再被砸,老人街邊吃飯遭圍攻
- light12:美國應給黑人賠償14萬億美元?加州已通過立法研究這錢怎麼賠
- yunmu:新冠肺炎暴發反映人類要學會和⾃然和諧相處
- qxw66:牛二印度
- 8288:好市多烤雞「嗑到剩骨架」才退貨








